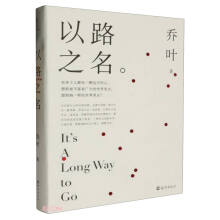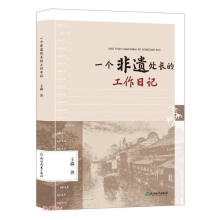我的收藏:牛汉先生著作
从1983年开始与牛汉先生通信至2013年先生仙逝,不知不觉30年。30年当中,先生给了我太多的诗教,使我受益很多。30年里,我得到先生所赠著作也不少,摆在书架上,已是堂堂正正一大排,每每凝望或翻阅这些著作,我都会想起许多往事。虽然记忆是零碎的、一点一滴的,但一个清白、刚直如大树般的诗人形象,是完整的,难以忘怀。
1982年2月9日,我在吉林省敦化新华书店买到一本《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这是一本20位诗人的合集。我那时刚刚学习写诗两三年,对新文学史了解得不多,“七月诗派”这一词对于我来说也很陌生,但我对牛汉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当时,敦化林业局有一位吴登荣老先生,他曾与牛汉先生短期共事。他对我说过,要写诗,应该结识牛汉,牛汉是一位真正的诗人。
1983年7月,我从东北移居华北,进入石油行业工作,单位的驻地在河北任丘,距北京150多公里的路程,我开始与牛汉先生通信,但一直没有与先生见面的机会。直到1984年5月,河北省在华北油田召开中青年作家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请来了一些著名作家和诗人,牛汉先生也被邀请来了。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与牛汉先生见面的当天晚上,我回到家中从书架上取出《白色花》,到牛汉先生的房间去,请先生题词、签名,这也是我第一次请名人题词。先生用钢笔在《白色花》书名页上写下了一行深蓝色的大字:“谢谢你阅读我们的诗!”我当时很激动,鼻子有些酸,我一下子想起这本书的序言结尾处引用诗人阿垅1944年写的两句诗:“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先生以及他们那一流派诗人的苦难历史了,并且已经开始大量地阅读“七月”诗了。
那天,我用一张洁白的复印纸给《白色花》包了一层书皮,倒不完全是怕把书弄脏了,主要原因是,我一看到那封面上红色的血流中生长出来的那一支白色花,心就被震颤着,就有热泪要流出来。(多年之后还知道了:书的封面是牛汉先生的儿子史果设计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包在书外面的那张白纸我一直没有换下来。1984年冬,我得到了一本牛汉先生签赠的诗集《温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5月版)。我无法控制住自己的心情,捧着《温泉》长时间没有打开书,我仿佛感到了这本诗集的重量。
那天晚上,我通宵未眠,先是逐字逐句地读了整本诗集,又逐字逐句地读了绿原先生为这本诗集做的序,绿原先生在序言中说:“这些新诗大都写在一个最没有诗意的时期,一个最没有诗意的地点,当时当地,几乎人人都以为诗神咽了气,想不到牛汉竟然从没有停过笔。”然后就是反复地把诗集中的那些诗读来读去。我读《硬茧颂》、读“你打开了自己的书——给路翎”时,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还有那些在后来的日子里长久地打动着我的诗,如《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温泉》《根》《巨大的根块》《鹰的诞生》《蚯蚓的血》《伤疤》等等。
P1-2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