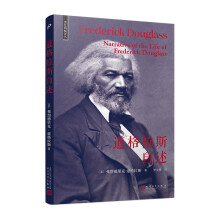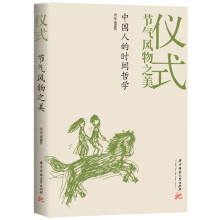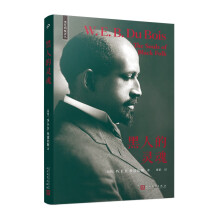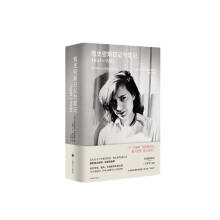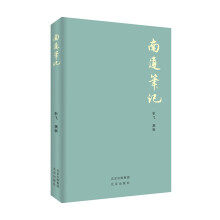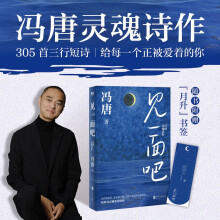《新疆是个好地方:一根葡萄藤》:
乡下人对苜蓿芽有着特殊的偏好。一到开春,苜蓿刚从地里露出新绿,那些勤快的主妇,便急不可待前去“掐尖”。苜蓿属于多年生草本植物,就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会长出新的一茬。只是韭菜生长频率快,一茬一茬照吃不误。苜蓿则慢得多,一年两茬,至多三茬,而且除了春天那一茬新芽外,稍一长老则不可食用。
先是一簇一簇,随后则一片一片,齐柞长的黄秆子,是去年的老茬,新芽就从老茬里长出来。以前苜蓿地都是集体的,因为面积大,季节性又太强,根本不用担心“供不应求”,苜蓿芽不够吃。都是为了尝个鲜,春天青黄不接,菜窖里的菜基本吃完了,关键是也吃腻了,除了羊角葱,其他新菜又稀缺,只能寄希望于苜蓿芽了。
苜蓿芽刚长出来,翠绿翠绿,一根茎脉分出几个叉,叉再派生几片叶,就像采茶一样,轻轻一掐,苜蓿芽就下来了,一点不费事,也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全凭心灵手巧。到了掐苜蓿芽的季节,地里就充满欢声笑语,清一色女人和孩子,手不闲着,嘴巴更是忙活,仿佛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享受着春天的馈赠。
掐回来的苜蓿芽,几乎不用拣,用水洗了,做凉菜和下饺子都好吃。那时候粮食紧张,肚子里油水也少,餐桌上有一盘苜蓿芽凉菜,饭就吃得有滋有味。做凉菜很简单,先用开水焯一下,再撒点盐,倒些醋就成了。苜蓿芽饺子最好掺和鸡蛋,我觉得味道比肉馅还要好。
小时候,母亲喜欢做苜蓿芽合子,大大的平底铁锅,上面抹一层菜籽油,随后把苜蓿芽合子放进锅里,捂上锅盖,过一会儿翻一下,等苜蓿芽合子熟了再一瞧,船形的巴掌大的合子,中间焦黄焦黄,还滋滋冒着油花,而周边则呈现一圈白色,仿佛事先描画好的,色泽非常鲜明。拿菜刀一分为二,盛在盘子里,一人一份,立刻感到清香扑鼻,回味绵长,把人吃得美滋滋的。
那种儿时妈妈的味道,到现在我也忘不掉。虽说住在城里几十年,可我一直怀念乡下的生活,尤其到了春天,估摸着苜蓿芽差不多长出来了,嘴就馋得难受。好在庄户人早已掌握透了城里人的喜好,什么季节供应什么新鲜土特产,包括苜蓿芽、黄花菜、榆钱子,甚至老鼠瓜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生活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可以这样说,随着城市绿化面积的不断扩大,一些原本生长在农村的植物,也已开始在城市安家落户了。一天路过一个三角地绿化带,就看到三三两两的女人,弓着腰,低着头,专心致志在地上采什么。我就问老婆:她们在于啥?老婆就摇头。我告诉她说,维吾尔族女的在掐苜蓿芽,而汉族女人是在挖黄花菜。
野蒜苗比苜蓿芽稍晚一些,生长环境比较特殊,必须是在水多的地方,譬如水渠边上草地里,同时还得遮蔽阳光,比方靠近大山的树林子。在我们芦草沟一带,似乎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磨石嘴子往上生长蒜苗子,朝下则没有。
野蒜苗也属多年生草本植物,颜色银白,喜扎堆,一撮一撮,韭菜一样叶子长,呈三棱状,很容易辨认。之所以称为蒜苗子,就是因为有大蒜的味道。一般喜欢凉拌,也有做成馅子,包包子,或者捏饺子,口味都比较特殊,说是蒜苗子却又像韭菜,二者兼而有之,值得回味。
最早知道蒜苗子,还是孩提时代,当时正在上初中,一天就听住在磨石嘴子附近一小队的同学说,一大队四队有一块“风水宝地”,那里的蒜苗子就像草一样,渠两边,树底下,长得到处都是,拔都拔不及。关键是那里还有我们最爱玩的“瓜瓜牛”,也就是蜗牛,干的湿的都有。我就心里痒痒,盼着春天快一点到来。到了第二年春上,先是跟着一小队的同学一块去,后来就和我们队上的同学结伴而行。
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五六公里路一点都不算长,中午放学吃口馕喝口水,连跑带跳一阵就到了。野蒜苗确实多,不一会儿就一人拔了一大堆,各自分别做了记号后,就开始再找“瓜瓜牛”。遇上千的,就相互“抵牛”,看谁的坚持时间最长。好的“瓜瓜牛”呈紫红色,螺旋状,看着就结实,握在手里硬邦邦的,尖对尖和对家一抵,一下一个小窟窿。而那种泛白色的,由于时间久了,遭到侵蚀,有些干脆手一捏就碎了。找到那些鲜活的蜗牛,我们就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要么一块石头上,要么一根干木棍上,最好再有一些光线,把蜗牛放上去,然后一起趴在两边,敛声憋气,等着蜗牛慢慢从壳里爬出来。很快,头顶着两根细肉角的蜗牛就钻出来了,拖着外壳一步一步向前爬,留下黏糊糊的印迹。有些孩子就沉不住气,翻起身要看个究竟,可是眼睛还没有凑上去,蜗牛立马脖子一缩,就退回到壳里了,再也不出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