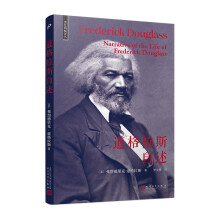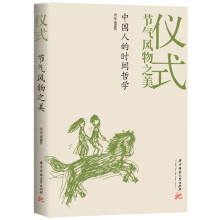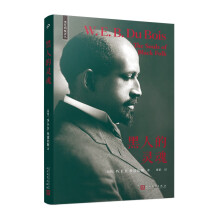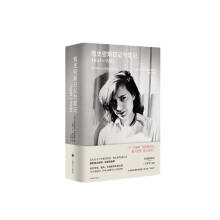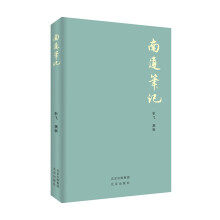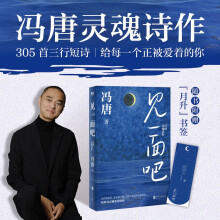《生命的河流》:
母亲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广东新会外海的陈家,外祖父陈鹿宾有12个兄弟,他们的父亲(即外太祖)和大儿子(母亲称大伯父)是清末同科中举的,一家在一个考场里出了父与子两个举人,这不仅在广东,就是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外祖父年轻时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农科。我曾问过外祖母(她的名字叫黄德联):“外祖父为什么要学农科呢?”她说那时候中国的农业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最大。我又问:“出国的费用怎么解决呢?”她笑着说:“还不是靠我的嫁妆和我做的女红,他说是跟我借。”当然外祖父后来也没有真的还。外祖母也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她从小与哥哥一起在私塾旁听,因此能识字,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1966年上半年,我在四川眉山搞“四清”时给她老人家写了一封信,她用毛笔回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信中她连二十四节气都能倒背如流,还鼓励我要多了解农村和农民。当时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军队的老粗,他拿了信先拆开来看,看了后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80多岁的外祖母所写,他很是感动,从此也改变了对我的印象。
外祖母活了93岁,一共生了12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我母亲排老四),在我母亲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不久又生了一个儿子。外祖父回国后,参与了仲恺农校的创建工作。多年曾任教务长的他,因连续生下众多子女,只靠他的工资也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他跟别人一起开办银行,还把何香凝先生的钱也吸纳了进来。后来银行破产了,据说这笔糊涂账至今也未还清。因为生活所迫和民族危机,我的姨妈和舅舅们大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外出谋生,并加入共产党。
日本兵侵占广州后,外祖父曾被要求出来参加维持会(因为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但他坚决不从,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穿着睡衣和拖鞋逃到澳门避难,后来他与仲恺农校的师生一起撤到粤北韶关的大山里继续办学。据说有一次,他自己一人外出爬山旅行,在瓢泼大雨中迷了路,三天三夜之后由几个农民把他背了回来,从此就瘫痪在床,抗战胜利后没几年就去世了。
那时候我的舅舅和姨妈们都在逃难和革命活动中成长,三姨妈带着最小的七姨妈在“国难幼儿园”中到处奔波,而二舅和四舅在他们十四五岁时就已成了共产党的交通员,除二姨妈和二姨父外,其他几个姨妈和姨父都是在革命的队伍中结婚的。但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都过得比较平淡,只有我的二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过新会县第一任县长,后来一直担任佛山地委宣传部部长。二舅口才极好,据说连续七小时的报告,他可以完全脱稿,并且让听众听得如醉如痴。二舅母则任佛山市委副书记二十年之久。外祖母一直生活在他们家中,我的母亲每年都要带我们几个后辈去看外祖母,每次和外祖母团聚在一起,就跟过节一样快乐。
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留学前夕,曾回广州见了一次二舅,并与他进行了交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而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才体会到,父亲曾说的我的某些气质与二舅有几分相似。
我的二姨父曾留学美国13年,多次寄回钱让二姨妈去美国团聚,而这些钱都被挪作家用了。二姨父回国后一直从事民主运动,是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任该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和连续几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直到其去世。
新会外海的陈家,最出名的文化人是陈原先生,柳亚子先生在写到我母亲时提到过。在辈分上他应叫我母亲为姑姑,因为他是举人(大伯父)的孙子。我在北大读书时,母亲曾来过一封信说这位前辈去广州家里看望过她,并嘱咐我有空可以去拜访他,要买什么书也可请他帮助推荐。当时这封信被同宿舍的同学看到了,说我可以走后门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反而不去拜访他了,后来“文革”来了,就更想不起去看望这位文化名人了。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我原本有一个可以聆听他教诲的机会。后来我买了他晚年所作的散文集,特别是我每期必读的《读书》杂志,我知道这是他在“文革”后与其他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共同创办的,并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如今每当我买到新的一期《读书》,就会想起他,他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是真心希望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和繁荣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