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芳了一片海
一
在春光四溢的午后,或秋风乍起的清晨,我曾独自一人漫游蟳埔。熟悉得仿若不存在的海洋气息无孔不入。簪花围的姑娘媳妇儿、阿婆奶奶们也习惯了镜头,她们或淡定地对着镜头微笑,或根本无视掌镜者的存在而自顾开蚵修网。在蟳埔,你很难看到无事闲逛的蟳埔女,簪花与劳作,成了她们生命的标签。
无法说清内心潮湿的原因。每次寻访,都像大海捞针似的,打捞被摧毁得所剩无几的记忆碎片,包括触摸那几幢残破不堪的蚵壳厝,眺望那若隐若现的海丝帆影。时空不可捉摸,每一次的回眸,都像在祭奠自己。
蟳埔村口,隔着丰海路,就是海。丰海路——东西贯穿城市的沿海大通道,把渔村、滩涂、大海割裂开来,也隔断了人与海浑然一体的原生态画卷,还好尚有海腥味从路旁一溜儿排开的鱼摊里飘出来。泉州靠海,市井十洲人吃海鲜成精,深知船刚靠岸,还没褪去海潮气息的海鲜,最地道,也最为妙不可言。鱼虾蟹们倘若离了海,就算在餐厅酒肆的氧气支撑下依旧活蹦乱跳,但其鲜香已大打折扣。至于那些跨了山水,空运速递到内陆以及北方的海鲜,虽金贵,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失去了海的初始记忆。因而丰海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到了蟳埔路段,会减缓行速,摇下车窗,探出一双双眼睛,在一框框、一篓篓活色生香的鱼虾蟹上巡觑。他们大都是吃上了瘾的老主顾,也有好奇的路人甲。
汽笛奏响凯旋的赞歌,靠港的男人们笑傲江湖,把一船的战利品甩给女人。女人腰挎红色塑料小包,身着斜襟大花衣、阔腿裤,头顶簪花围,笑盈盈地迎接海上冒险者归来。她们的手舞蹈般,幻化出一道道缤纷的虹,一大船几百上千斤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鱼虾转眼间分门别类,一筐筐一箩箩,尘埃落定。
听着涛声长大的蟳埔女,虽然不敢去驾驭茫无边际的浩渺大海,但海对她们永远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她们从不错过任何亲近海的机会。在妻子的鼓动下,夫妇俩驾一条船去讨小海,几十海里,一个潮汛,一天一个来回,收网时也有三两百斤的鲈鱼、小杂鱼、虾姑、虾等。虽让远征者不屑,也比不上男人远洋搏击时大海几千上万斤的慷慨馈赠,但因为有了女人们在浅海撒网、滩涂劳作,让我们享用了更鲜爽、更多样化的海上珍馐。令人怅惘的是:当年几千平方米的开蚵广场消失了,海港也沦为城市腹地。你享用了鱼虾的鲜美,却无法见证风浪的险恶,包括你对海一厢情愿的浪漫臆想。
除去休渔期及天气原因无法出海,蟳埔男人一年的出海时间实际也就四五个月。其余时间就做散仙,四处晃荡,打麻将,喝烧酒,享受高高在上的王者待遇。女人累得头晕目眩,倘若不小心抱怨一下,马上遭到一顿抢白:“做这些婆婆妈妈的小事喊什么辛苦?有本事你出海打鱼去!”远征归来的男人永远是渔村的主宰,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也是的,没有他们挑战险恶的大海,哪来的鱼虾满舱?哪来的日子殷实?因为对大海的敬畏,所以敢于征服大海的男人有了神明般的威慑力,在蟳埔男人面前,蟳埔女只能俯首称臣,尽管她们的付出是男人的无数倍。
有一回去惠安,和一帮文友乘机动船到一个小岛上。那日启航时海温和恬静,可是傍晚回航时,许是我们一船的喧嚣惊扰了海的梦,它脾气拗上来了。从海的腹腔传出的闷响冲出海平面,海激荡着,怒吼着,扑向我们的机动船,几米高的浪花冲进船舱,把一船二十几个人淋得像刚打捞上来的鱼虾。船激烈颠簸着,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翻个底朝天。巨大的恐惧像绳索般勒得我几乎窒息。好在船快靠岸时,风平浪止,一颗蹦出的心总算收回。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我像获得重生般大喊:“大海太可怕了!”船老大瞥了我一眼,冷笑着说:“在海上谋生,这根本不算什么!”始信那句话——行船讨海三分命!也顿悟在渔村,男人头上顶的是勇士的光环。在男人眼里,女人们是滩涂上的花蛤、海蛎之流。男人只关注大海,女人得承担一切。女人骨子里也把自己看轻。她们低眉顺眼,任劳任怨,像永不疲倦的小蜜蜂;她们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收拾出一个像模像样的家,煮出一桌子香喷喷的饭菜,却没有资格和男人一起上桌吃饭,而是拿个碗,装碗饭,蹲旮旯处吃去。“小时候觉得我妈妈很可怜,在家里很没地位!因为妈妈连生两个都是女孩,所以太奶奶对她冷眉冷眼,很不待见。”蟳埔女黄丽泳说起自己的妈妈和太奶奶,一声喟叹,“当年太爷爷抛弃大陆的妻儿,去了海峡对岸,另娶台湾查某,太奶奶独自一人撑起一个家,也很可怜。”太奶奶是个要强的女人,她佯装微笑,伸手接住命运的不公,满头霜雪与耀眼的簪花围交织着生存的坚韧与绚丽。
“我爸爸妈妈感情不错,但爸爸永远觉得太奶奶是对的!”黄丽泳语带伤感,“妈妈生下我妹妹时,太奶奶简直要发飙了!别人家媳妇坐月子有鱼有肉,我妈妈连饭都吃不饱,太奶奶还到处张罗着要把我妹妹送给别人。”现实就是如此,蟳埔媳妇如果生不出男娃,在家里、村里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在他们看来,没有男孩,不但意味着家族无后,更宣告家族与大海的较量自动缴械投降,在蟳埔无立锥之地。难怪老太太对孙媳妇各种刁难,她对曾孙女说得最多的话是:“女孩子能吃饱就好了!”一生吃尽千般苦头的老奶奶把自己的不幸无形地转嫁到自己至亲的女性身上。一代一代的蟳埔女陷于这种因袭而成的顽固意识里,复制粘贴着自己的命运,却浑然不知自己就是自己不幸的炮制者。
男人把家园托付给女人,女人则把梦想交予出海的男人。女人们接纳海的馈赠,也把生活的酸甜苦辣收入囊中。然而,生活中细如牛毛的琐杂,没完没了的烦恼,果真是弱女子的肩膀能挑得动的吗?如果让你选择,你愿意生为男人,还是女人?根本没得选择!生存的本质就是解开接踵而来的一道道难题。没有办法把握的每一次出海,没有办法预料的每一道坎儿,像一个个魔咒,压在命运之上。唯一可行的是找一个出口。于是男人纵酒欢歌,肆意挥霍,尽情裸露海的子民的英雄本色。女人则小心翼翼地把自己培植成一朵花,种在泥土里,植入灵肉里。
悲欢被小心隐匿,苦难磨出了珍珠般的光芒,浸红花蕊,组成繁枝琐节招摇于头顶。一朵朵明艳的花,是一群舞蹈的精灵,是光阴的叠加和累积,是等待心上人劈波斩浪而来的腼腆。纵使老了红颜,褶皱里仍荡不去层层闺阁秘密。就像压箱底的红装,抖出来,绵绵密密仍是少女的娇羞。红装、花蕊、甜蜜的梦,在蟳埔,不受时空限制。从牙牙学语的小娇娃,到白发苍苍的老阿婆,都可衣衫明艳,移步生香。耕海耘田的累,养儿育女的苦,操持家务的忙,都化作簪花围的千般光华,万种风情,哪里还有空暇指责命运的层层盘剥?单是头顶那层层叠叠的花,就得投进多少心思?衍生多少甜蜜?骨髻、渔梳、红绳、小把簪、玫瑰、玉兰、含笑、雏菊、粗糠、素馨……每一个季节,都得翘首以盼,采撷含苞待放的美;每一个罅隙,都得穿针引线,裁剪独具一格的韵。
蟳埔女用花做成面罩伪饰自己,她们看上去花一样柔弱,骨子里却有大海一样的硬气。她们貌似活在大海一样嚣张的男人的阴影下,可她们低下头颅时,也正是她们掌控一切时,她们才是蟳埔真正的主人!更确切的表述是,她们是大海真正的主人!男人们以为,天下事除搏击大海之外,其余皆是小事,也是他们所不屑的。所以蟳埔的日常生活,男人是缺席的。他们不管事,不管钱,号称天子实则大权旁落。女人摸黑把一大船的海鲜分拣清楚,或在船上、岸边直接交易,或批发给鱼商,或天蒙蒙亮就挑担进城摆摊设点、沿街叫卖。蟳埔女生来就是做生意的料,她们笑吟吟的,招揽顾客,称重干净利落,算账分毫不差。当她们揣着鼓囊囊的钱包火急火燎地赶回家时,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等着她呢。柴米油盐、人情往来、生儿育女、垒屋造田,哪一样不是她们在劳筋骨、费心思呢?而当禁海休渔期,或忙碌的空隙,蟳埔的花事与大海的波浪一样,装饰着每一个日子。
蟳埔女与花,彼此相惜。在与命运无止无休的对抗中,花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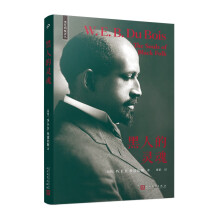






——著名作家、《文艺报》总编辑 梁鸿鹰
姚雅丽用委婉、蕴蓄的笔调,鲜活、跳跃的文字呈现了现代与古典的方方面面。笔到之处,飞花溅玉,真实可感而不虚无缥缈。其行文的格调和为文的情趣独具一格,带给读者充实饱满的精神碰撞和回味悠长的品读思考。
——散文名家、《美文》副主编 穆涛
姚雅丽自觉地把笔触伸向闽南这片沃土。闽南元素、海丝史迹在她的文章里自由穿行。你可以从她的文字中嗅到刺桐花开的芬芳,听到海丝浪涌的激越。挖掘、汲取、传承,使她的文章富有使命感和厚重感。不懈的求索让姚雅丽超越了一般文人的闲适,且通过辐射和带动,形成一种崭新的人文氛围,并和泉州的深厚文化积淀相融合,形成了闽南文人独特的人生景观。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邱华栋
作为一名闽南女性,雅丽的写作打上了清晰的地域烙印。乡土的质朴和极速嬗变,行将消失的民俗、信仰、祭祀,小镇的浓郁风情,闽南的山光水色都在她的笔下隐约可见。从闽南乡镇走进温陵古城,雅丽不断地把心中的传统与质朴融入到现代的感情和体悟,并投注于文字之中。文学或许是她活在时光里的另一盏灯,一种理想化的象征。当然,还有现实生活中她独立的人格和不懈的追求。因而在她的作品中,你看不到多少悲哀的东西,多少晦涩的阴影,更多的是看到雅丽作为闽南女性的坚韧、倔强和善良、美好。她把明媚的笑容送给你,把艰辛苦涩消融于时光深处。这就是雅丽,永远保持轻盈的姿态,永远善意地呈现人与事之间的关系,亦由纷繁中梳理出天地自然造化的灵机与训诫。
——著名作家、评论家 孙绍振
雅丽的《香水与爱情》不仅是她个人的突破,更是泉州作家在散文创作上的突破!
——著名作家 陈志泽
以情动人,是作品的外在表现力,蕴于其里的当是作家心灵与人生的真诚对话。发现表达的审美对象,则源于作家对生活具象的艺术感受力。姚雅丽的散文讲究构思立意和生活画面的铺排。文学艺术的生命力,在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情到深处自然真。姚雅丽的作品,zuida的成就便是倾注感情,并巧妙地把读者带入她精心构筑的艺术空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蔡飞跃
有些人的文章,你初看两三篇觉得还可以,再看几篇就觉得没什么好看了。而雅丽的文章无论写什么都有发现:发现生活的可爱之处,发现爱情的种种真谛,发现美的东西随处可见。这样,就使得她的文章耐人寻味了。当然,雅丽她并不刻意寻得什么,也不想忘却什么,她就这样漫无边际地在生活里,在文字中游荡着,在落叶轻扬的时候。她收获了什么,回忆了什么,其实都无足轻重。因为“一切逝去和不曾逝去的悲伤,有着销魂蚀骨的美丽。”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泉州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蔡芳本
姚雅丽,文如其人。她的散文独具魅力,读过她的第一篇作品,你就有了想读她第二篇、第三篇的强烈欲望,诱惑性极强,令人欲罢不能。本人是姚雅丽老师百分百的忠实“粉丝”。
——文友 杨发胜
花是大自然恩赐的造化,世人爱花,常把女人比作花,这是对女人的尊宠。女人花有百媚千红、风情万种,而世界上每个女人都有自己的颜色,不仅在外表,更在内心,在那深幽的世界里,一朵鲜嫩的花儿正丰润起来,那是心血浇灌出的美丽,她与众不同,清香而神秘,属于自己。当人们发现并嗅到她文字里的芬芳时,慢慢被她吸引住了,快乐就会如此鲜亮、爽朗乃至透明起来。
——文友 叶林
雅丽总是在不经意间,把我们心底想说又不知如何表达的话语轻轻地说出来,让你在感慨万千中佩服她敏锐的洞察力和温柔细腻的文笔。雅丽的文章是一种温文,一种美文,是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清澈,毫不造作,在情感的流露中自然生成。即便是精心构造的意境也不会让人觉得她在构造。古人所谓的“妙笔出天然”应该就是雅丽这种文风吧。
——《天下石》主编 李妙莲
画面上的人儿,笑意盈盈,徐徐走出来。恍惚间,辛弃疾的“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跳入脑海。美,总是引人注目的。我常常从背后偷偷地欣赏她。长发披肩,窈窕多姿如风摆杨柳。轻轻的,亮丽,浑身散发着一种不能言说的迷人气息。顿时心生羡慕:上帝把你造就得美就美了,偏你还如此爱美,偏你还如此青春,偏你还能写得如此好文章。
——诗人 柯秀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