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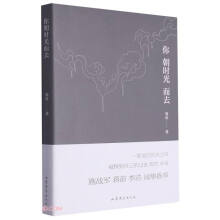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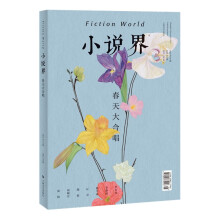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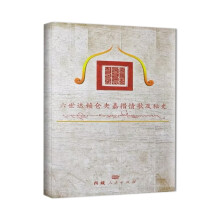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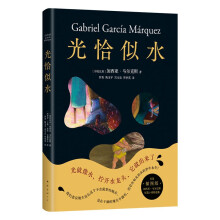



小说集《无处诉说的生活》共收录十二篇小说,包括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将军的部队》。作者毫不吝啬地剖析生活的残忍,从日常琐事中挖掘人性。李浩以他特有的平静沉稳的叙述方式将读者推向风暴中心,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涌潮生,我们身处生活之中,谁也无法逃离被围困的命运。
将军的部队
我老了,现在已经足够老了,白内障正在逐渐地蒙住我的眼睛,我眼前的这些桌子,房子,树木,都在变成一团团的灰色的雾。眼前的这些,它们已在我的眼睛里逐渐地退了出去,我对它们的认识都必须依靠触摸来完成—有时我看见一只只蝴蝶在我的面前晃动,飞舞,它就在我的眼前,可我伸出手去,它们却分别变成了另外的事物:它们是悬挂着的灯,一团棉花,一面小镜子,或者是垂在风里的树枝。
因为白内障的缘故,我把自己的生活处理得混乱不堪。几乎所有的物品都不在它应该的位置,水杯和暖水瓶在我的床上,拐杖则在床的右侧竖着,而饭勺,它应当在我的床对面的茶几上……我依靠自己在白内障后手的习惯来安排它们,所以我房间里的排布肯定有些……有许多本来应该放在屋里的东西,因为我的手不习惯,它们就挪到了屋外。就是这样,我的屋子里还不时会叮叮当当,我老了,自己刚刚放下的东西马上就可能遗忘。我说我的生活处理得混乱不堪还有其他的意思,现在就不提它了。好在,这种混乱随着我走出屋去而有所改变,我离开了它们,我就不再去想它们了,我觉得自己还有许多的事情可想。我坐在屋檐下。别看我的眼睛已被白内障笼罩了,但我对热的感觉却变得特别敏感,我能感觉热从早晨是如何一点点地升到中午的,它们增加了多大的厚度和宽度。
我坐着的姿势有点像眺望。
我坐着的姿势有点像眺望,是的,我是在眺望,别看我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可旧日的那些人和事却越来越清晰,我能看清三十年前某个人脸上的每一条皱纹,我能看清四十年前我曾用过的那张桌子上被蜡烛烧焦的黑黑的痕迹。我坐在蜡烛的旁边打瞌睡蜡烛慢慢地烧到了尽头可我一无所知。我甚至没有闻到桌子烧着后焦煳的气味。
我坐在屋檐下。我坐在屋檐下,低着头,低上一会儿,然后就向一个很远的远处眺望。当然,白内障已不可能让我望见远处的什么了,我做这样的姿势却从来都显得非常认真。我的这个动作是模仿一个人的,一个去世多年的将军的,这种模仿根本是无意的,只到三个月前我才突然地发觉,我的这个动作和将军是那么的相像。
我越来越多地想到他了。
想到他,我感觉脚下的土地,悄悄晃动一下,然后空气穿过了我,我不见了,我回到了将军的身边,我重新成了干休所里那个二十一岁的勤务员。
想到他,我的患有白内障的双眼就不自觉地灌满了泪水。我已经足够老了,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能听到死神在我身边有些笨拙和粗重的喘息。我没什么可惧怕的,更多的时候我把它当作自己的亲人,一个伴儿,有些话,想起了什么人,什么事,就跟它说说。想起将军来的时候,我就跟它谈我们的将军,谈将军的部队。别看它是死神它也不可能比我知道的更多。
将军的部队装在两个巨大的木箱里。向昔日进行眺望的时候,我再次看见了那两个木箱上面已经斑驳的绿漆,生锈的锁,生锈的气味和木质的淡淡的霉味。
对住在干休所里,已经离休的将军来说,每日把箱子从房间里搬出来,打开,然后把刻着名字的一块块木牌从箱子里拿出来,傍晚时再把这些木牌一块块放进去,就是生活的核心,全部的核心。直到他去世,这项工作从未有过间断。
那些原本白色的,现在已成为暗灰色的木牌就是将军的部队。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说清这些木牌的来历。我跟身边的伴儿说的时候,它只给了我粗重的喘息,并未作任何的回答。我跟他说,我猜测这些木牌上的名字也许是当年跟随将军南征北战的那些阵亡将士们的名字吧,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可后来,我在整理这些木牌的时候,却发现,上面有的写着“白马”“黑花马”“手枪”,而有一些木牌是无字的,很不规则的画了一些“O”。也许,将军根本不知道那些阵亡战士的名字?
我用这种眺望的姿势,望见在槐树底下的将军打开了箱子上的锁。他非常缓慢地把其中的一块木牌拿出来,看上一会儿,摸了摸,然后放在自己的脚下。一块块木牌排了出去。它们排出了槐树的树荫,排到了阳光的下面,几乎排满了整个院子。那些木牌大约有上千个吧,很多的,把它们全部摆开可得花些时间。将军把两个木箱的木牌全部摆完之后,就站起身来,晃晃自己的脖子,胳膊,腰和腿,然后走到这支部队的前面。
阳光和树叶的阴影使将军的脸有些斑驳,有些沧桑。站在这支部队的前面,将军一块块一排排地看过去,然后把目光伸向远处—我仍然坚持我当年的那种印象,将军只有站在这支部队前面的时候才像一个将军,其他的时候,他只能算是一个老人,有些和善,有些孤独的老人。将军从他的部队的前面走过去他就又变成一个老人了,将军变成一个老人首先开始的是他的腰。他的腰略略地弯下去,然后坐在屋檐下的一把椅子上,向远处眺望。他可以把这种眺望的姿势保持整整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现在我也老了,我也学会了这种眺望的姿势,可我依然猜不透将军会用一天天的时间来想些什么。可能是因为白内障的缘故,我眺望的时间总不能那么长久,而我有时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坐着,待着,用模糊的眼睛去看。我想将军肯定和我不一样,他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的生生死死,他肯定是有所想的。
我老了。尽管我不明白将军在向远处望时想的是什么,但我明白了将军的那些自言自语。他根本不是自言自语,绝对不是!他是在跟身边的伴儿说话,跟自己想到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说话,跟过去说话。就像我有时和将军说会儿话,和我死去的老伴,和死神说话。当年和将军我可不是这样说的,尽管他对我非常和蔼,可我总是有些拘束,和他说话的时候用了很多的精心。现在,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多年的朋友似的,我和他都是一样老的老人了。
帮将军把两个木箱搬出来,我就退到某一处的阴影里,余下的是将军自己的事了。将军摆弄他的那些木牌的时候,我就开始胡思乱想。这种胡思乱想能让时间加快一些。在没有胡思乱想时,我就用根竹棍逗逗路过的虫子和蚂蚁,或者看一只蝉怎样通过它的声音使自己从稠密的树叶中显现出来。将军的那种自言自语一片一片地传入我耳朵,其中,因为胡思乱想或别的什么,不知自己丢掉了其中的多少片。我耳朵所听到的那一片一片的自言自语,它们都是散开的,也没有任何的联系。
将军说,你去吧。
将军说,我记得你,当然。我记得你的手被冻成了紫色。是左手吧?
将军说,你这小鬼,可得听话呀。
将军说,我不是叫你下来吗。
将军说,马也该喂了。
将军说,……
在我回忆的时候,在我采用眺望的姿势向过去眺望的时候,我没能记住将军说这些话时的表情,但记下了他的声音。他的声音会很突然地响起来,然后又同样突然地消失。我常在他的声音里会不自觉地颤一下,突然地放下我的胡思乱想和手中的竹棍,我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
有两次将军指着木牌上的名字问我,赵××你知道么?王××呢?你清楚刘×的情况?……我只得老实地回答,我不知道,将军。
哟。将军有些恍然和茫然的样子。那两次问话之后我都能明显地觉察出将军的衰老。看我这记性。将军一边望着他所说过的名字一边摇头:人真是老了。我怎么想也记不起他们来。可我总觉得还挺熟的。真是老了。
他用手使劲地按着眼角上的两道皱纹。
1 将军的部队
13 爷爷的“债务”
49 一只叫芭比的狗
60 旧时代(三篇)
81 蜜蜂,蜜蜂
94 在路上
109 给母亲的记忆找回时间
136 一次计划中的月球旅行
266 灰烬下面的火焰
181 那支长枪
204 父亲,猫和老鼠
218 无处诉说的生活
李浩的小说不仅有精确的技术,还有狠忍阴鸷的力量,能够迫近事物的核心,专注“死的艰难”和“生的艰辛”,对人的生活状态提出存在意义的质询,属于“七十年代人”写作的又一类型。
——李敬泽
李浩的小说有鲜明的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他继承了先锋文学的遗产,特别是在叙事策略上,他癫狂地沉迷于复杂、颠覆、往复或拆解之中。因此,李浩的小说少有同时代作家那种鲜明的群体特征或时尚与肉感。
——孟繁华
从李浩的写作中我们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诗人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所创造的语言的存储者,这个语言的密码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甚至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将这个密码遗忘和丢弃。
——吉狄马加
李浩的笑意里有一种拙朴,或者说,是一种经思考却不世故的天真之气,一种宅心仁厚的人才有的气息。在这个意义上,李浩不是忘记了昆德拉的嘱托,而是结合自身的朴厚性情,写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幽默:就像写姑姑的舔食,内中也含着他的宽厚,那是属于他自己的,特有的不忍。
——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