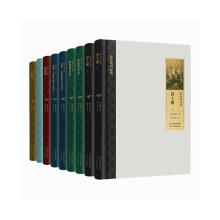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拼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
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
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
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