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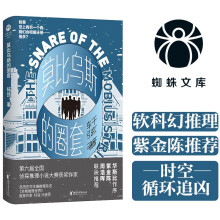




一、生态批评的发展概览
生态批评是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相融合的产物,是文学研究的“绿色转向”,是文艺批评界第一次涌现的对现实生态危机最广泛、最全面、最深刻、最激烈的回应。生态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发轫于英美两国,经历二十多年的漫长孕育期后,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在英美迅速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文学批评运动,其理论形态也趋于成熟,不仅具有明确的生态哲学基础、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实践,而且还建构了一套相对完整、开放的批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批评方法。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生态学者们对生态危机文化根源的诊断尚算全面,指出的问题也发人深省,所提出的应对危机的文化策略尽管有时显得天真、激进,但似乎也合情合理。其兴起的直接动因是威胁人类生存、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危机,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走向成熟的当代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其产生的学术背景是当时回避现实、画地为牢、追精逐致、孤芳自赏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已四面楚歌、难以为继。
随着全球生态严峻形势的扩散,生态批评迅速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性多元文化绿色批评潮流。跨学科是其基本特征,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是其显著特征。总的来看,生态批评近五十年的发展并非井然有序地展开,而是磕磕绊绊、几经周折。迄今为止,其大致经历了三次生态“波”或曰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态中心主义哲学推动下生态批评学派的创立及其理论建构时期,即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972—1997);第二阶段是生态批评的环境公正转向时期,即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形成与发展时期(1997—2000);第三阶段是生态批评的跨文化、跨文明传播,即“跨越性”生态批评的形成与发展时期(2000—),这里的“ 跨越性” 指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
第一阶段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为思想基础,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透过跨学科的视野,形而上地探究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涤除文学、文化中形形色色的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因素,深挖其中的生态内涵,旨在“绿化”文学和文化生态,具有浓郁的生态乌托邦色彩。
随着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美国草根环境公正运动的深入开展及其国际化传播,作为生态批评主要思想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学,遭到了以有色人种、穷人为主体的群体,第三世界以及生态哲学内部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和社会生态学学者的严厉批判,指责其专注于自然生态保护,忽视社会生态中因为肤色、性别、阶级及文化等因素的差异而遭受环境歧视的弱势群体,生态批评似乎也因此遭遇“十面埋伏”的窘境。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部分生态批评学者顺应环境公正之诉求,将环境公正引入生态批评学术活动之中,推动了生态批评的转型,过渡到了其第二阶段——环境公正生态批评。
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不是简单抛弃前一阶段的批评理论,而是疾呼拓展其研究视野,力荐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吸纳生态中心主义视野,透过种族/ 族裔、性别,甚至阶级的视野,结合各自独特的环境经验,检视文学、文化、艺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建构多元文化生态批评,探寻解决危机的多元文化路径。明确地说,环境公正生态批评主要增添了两个考察文学、文化生态的视野——种族/族裔视野和性别视野,有时也纳入阶级视野,当然,种族/族裔视野是基本的观察点。有鉴于此,除了环境公正理论以外,生态哲学中的另外两个哲学派别——生态女性主义和社会生态学也成了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
正当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出现不久,大约在新千年之交,有学者对它发难,指责它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并严重制约了其发展与深化。明确地说,意欲用“更具比较意识、更具跨国意识的方法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的强烈冲动也开始抬头”,其后续发展势头迅猛。具体来说,生态批评的发展过渡到其第三阶段——“跨越性”生态批评。当然,尽管作为生态批评基本特征的“跨学科性”得到了进一步拓宽,但在此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跨文化、跨文明”。根据生态批评后来的发展来看,所谓的“跨文化、跨文明”既指英美生态批评跨越其地理边界,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对其他国家的文学进行生态研究,也指英美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学界以及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非西方国家学界对英美生态批评的回应和在比较中建构富有自身文化特色的生态批评理论及开展的相关学术研究。当然,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英美以外的各个国家生态学界立足各自的文化立场对自己的生态文学进行研究,以凸显其环境经验的独特性或异质性。
由此可见,“跨越性”生态批评对生态文学的研究更具生态学术意义、生态审美价值及生态文化价值,因为这种研究更能充分彰显生态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之间的互动共生,真正落实生态文化多元性的原则,进而为跨文化、跨文明生态对话搭建深度沟通的平台。在此,笔者将对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学及环境公正理论做简要介绍,以期深刻、全面地理解生态文学内涵的丰富性,领略生态美的多样性。
二、生态批评的主要理论基础
(1)深层生态学
当代生态中心主义哲学认为,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人类文化的危机,人类主宰地位的危机,人类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的危机。要从根源上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主导下的生存范式,并向生态中心主义的生存范式转变。这种转变也是从主导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笛卡儿-牛顿机械论世界观向非人类中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这种生态中心主义世界观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形成了挑战,深刻地影响、启迪着陷入困境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催生了激进的生态中心主义文学研究范式,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学观,并成为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理论的思想基础,以期让生态中心主义成为建构生态型人类文化的文化动力。
当然,生态中心主义哲学内部也存在多种派别,其中,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是其最为激进的一派,也是第一阶段生态批评的核心思想基础。1973 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在其《浅层生态运动与深层、长远生态运动:一个概要》(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 一文中首次提出“深层生态学”的概念,后经其他多位哲学家阐发和丰富而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哲学派别。该派别采取了“理性的、全景的”(total-field)的观点,彻底抛弃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处于环境的中心的形象”,而采取更整体的和非人类中心的观点与方法。
深层生态学包括两条根本性原则,即“大我的自我实现”原则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所谓“大我的自我实现”,是对现代西方流行的“自我实现”概念的超越。现代西方流行的“自我实现”中的“自我”是一种与自然分离的自我,其旨在追求享乐主义的满足感。实际上,人不是与自然分离的个体,而是自然整体的一部分。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的“自我”是形而上的“自我”,其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或“小我”到“社会的自我”,从“社会的自我”再到“形而上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又可以称为“生态大我”(Ecological Self),它不仅包括“我”,一个个体的人,而且包括全人类,包括所有的动植物,包括热带雨林、山川、河流和土壤中的微生物等。
因此,“自我实现”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达成的。所谓“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 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 大我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中完成“小我的自我实现”的诉求。即是说,在生态系统中,一切生命体都具有内在目的,都具有内在价值,都处于平等的地位,没有等级差别,人类不过是众多物种之中的一个,在自然的整体生态关系中,既不比其他物种高贵,也不比其他物种低贱。这两条根本原则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实现,有人认为它在拒斥人类中心主义时,有矫枉过正之嫌,隐含反人类的冲动,可奈斯仍称之为“生物圈的核心民主”。
(2)生态女性主义
1974 年,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弗朗索瓦兹·德奥波妮(Françoise D’Eaubonne,1920—2005)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旨在论证女性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之间的紧密关联,号召广大妇女发动一场拯救地球的生态革命。后来,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被美国学者卡伦·J. 沃伦(Karen J. Warren)、澳大利亚学者瓦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等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称为女性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并发展成为激进环境哲学派别中重要的一支。该运动主张对传统女性主义的修正、继承、超越与发展,其间既有与社会生态学之间的冲突与对话,也有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与超越,更有对自身理论与实践的不断修正与完善,因此,生态女性主义是在充满对立与冲突的环境中逐渐发展成熟的,绝非是对其他理论进行“剪刀加糨糊”式的简单拼凑,相反,它放射出与其他环境哲学伦理迥然有别的批判锋芒,显示出独特的环境伦理建构力量。
作为激进生态哲学的一支,生态女性主义内部也派别林立,各派别之间观点常常有异,甚至相互冲突,要给它下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实属不易,但卡伦·J. 沃伦对它的界定似乎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在她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伞状的术语,它包括了多种认同在统治人类社会体制中对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尤其是对妇女的统治与对非人类自然的统治之间存在本质关联的多元文化视角”。也就是说,生态女性主义旨在探讨男人统治妇女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实质。它根源于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等级思维、价值二元论和统治逻辑。任何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环境伦理都是不充分的。随着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探讨范围也不断扩大,性别关系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男、女两个性别之间关系,而涵盖所有性别之间的关系,诸如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及双性恋等,这样,生态女性主义中的“女性”视野也拓展为涵盖各种性取向的“性别”视野,“酷儿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也随即应运而生。
由此可见,生态女性主义所追求的不只是女性与自然的解放,而是一切“受压迫者”的解放,是对“统治逻辑”的一切表现形式的拒斥,最终实现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世界的永续的和谐共生。
(3)社会生态学
作为激进生态哲学的一支,社会生态学也像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一样在思考、理解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世界的关系时,倡导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它们都更为具体地探讨了导致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都认为“统治自然”是更为宽广的支配与控制取向的社会网络的一部分,除非各种统治形式被确认并被消除,否则在环境危机面前,我们将无所作为。然而,它们之间的核心区别在于认定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性统治形式不同,因此探寻的应对生态危机的文化和现实路径也迥异,也由此确立了各自在学术界的合法地位。
具体来说,深层生态学锁定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生态女性主义将父权制,或者说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与人对自然的统治之间的内在关联,看成是导致生态问题的根源性问题;而社会生态学则认为社会中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和社会统治才是导致人对自然统治的根源。也即是说,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统治的延伸,生态失衡是社会失衡的客观对应物。美国哲学家、社会生态学的创立者和主要理论家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1921—2006)就认为社会等级制与支配自然的理念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在他看来,作为历史事实,等级制社会鼓励人们用对非人类自然世界的控制能力来判断社会的进步。最终,这种联系相互强化,恶化了社会生态,强化了人对自然的盘剥。因此,要根除生态问题,必须首先从解决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等级制和压迫性的社会体制着手。
(4)环境公正理论
美国著名的公民权利领导人、基督教联合教会争取种族公正委员会执行负责人本雅明·查维斯(Benjamin Chavis)于1987 年发表了环境公正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美国的有毒废物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关于危险废物场所的种族和社会经济特征报告》(Toxic Wastes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National Report on the Racial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ies with Hazardous Waste Sites)。在该报告中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种族问题是全美居民社群与有害物质压力关联的主要因素”,并首次提出了“环境种族主义”(environmental racism)这个术语,以凸显环境压迫与种族问题之间的纠葛。1991 年,300 多名来自美国、加拿大马绍尔群岛,以及中美洲、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首届有色族人民环境保护领导人峰会”(The First National People of Color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Summit),会议旨在协调全球有色人种社群的环境立场,坚决反对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殖民主义,尊重和颂扬关于自然世界的各种文化、语言及信仰,确保环境公正,重建人与神圣大地母亲之间在精神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表达了重建人与大地母亲和谐关系的强烈愿望,议定并通过了“十七条环境公正原则”b。这十七条原则实际上就是有色族人民的环境公正宣言,是指导环境公正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也是环境公正理论的奠基之作,正式宣布了“环境公正”人士与主流环境主义者不同的环境立场。
具体来说,环境公正既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族群/ 族裔、性别、阶层、区域及文化社群之间,也指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环境资源、环境负担和环境责任上的平权,反对一切形式的环境剥削和环境不公。所以环境公正包括国内和国际环境公正。其中,种族范畴是核心,种族文化视野是基本的观察点。西方主流文化的白色种族霸权源远流长,种族歧视根深蒂固,因而种族主义与自然歧视之间的合谋往往成为“常态”,不仅或隐或显地体现在官方的环境制度和环境政策的方方面面,而且还广泛地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有鉴于此,曾经仅作为公共环境政策核心议题之一的环境公正终于在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被引入生态批评领域,并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立场,环境公正生态批评就是它向学术延伸的结果,旨在揭露和涤除形形色色的环境种族主义行径。在国际上,非西方生态学者力争站在环境公正的立场,透过各自的文化视野,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生态同仁开展跨文化、跨文明的生态对话,一方面要发掘自身文学尤其是生态文学的生态内涵,构建自己的生态批评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揭露和反对全球北方大国针对南方弱势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行径,探寻能构建普遍公平的、可持续的生态和谐世界的多元文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