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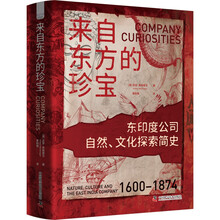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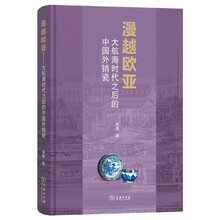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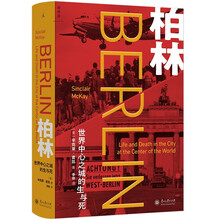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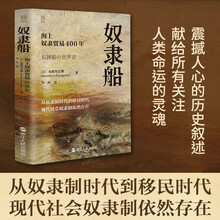
* 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森·沙曼力作。
* 颠覆欧洲中心论,以全球史观全新解读欧洲扩张。
* 《棉花帝国》作者斯文·贝克特盛赞推荐。
* 深入理解当前世界格局的来源与走向。
欧洲人曾在全球建立起霸权,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自1492年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就开始利用“坚船利炮”所向披靡地征服世界了。
这种认知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长久以来西方学者对欧洲扩张与西方兴起的解读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尤其近几十年来,对于欧洲扩张,西方的流行观点是近代早期军事革新所产生的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这符合史实吗?
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杰森·沙曼说,这种主流解释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存在太多的想当然。它夸大了近代早期欧洲的军事优势,将欧洲扩张视为一帆风顺的必然胜利。
作为典型的欧洲人,杰森·沙曼试图放下傲慢与偏见,去戳穿“军事革命论”的神话肥皂泡,尝试讲述欧洲扩张与世界新秩序建立的真实故事。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1500年后,在海外征服中,欧洲人会利用军事革命的成果,如近代作战方式战胜敌人。真实的故事是,在1500年至1750年的250年,并不存在西方军事霸权。由于并非政府正规军、人数太少和地理环境不同,欧洲扩张力量很难实施近代作战方式。比如有趣的是,西班牙人征服美洲的绝大多数战斗是近身作战,他们靠钢剑和盔甲这两种中世纪的装备而不是火药武器占据优势。且当地盟友的帮助至关重要,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特拉斯卡拉人提供军队,并建造和运输用来攻击的小船,西班牙征服者未必能攻下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近代早期欧洲人遭遇非西方政治体时,一副生杀予夺的高高在上的模样,对方只能俯首臣服。真实的故事是,在近代早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征服者靠的是“敬而从之”战略,才在非西方政治体的宽容、许可下立足、维持下去。欧洲征服者以恭顺态度相待的对象不仅有莫卧儿帝国、明清中国、德川幕府等东方强权,也包括非洲的若干政权。
人们想当然地认定西方与非西方的交流依循前者发出挑战、后者被动回应的挑战—回应模式。真实的故事是,双方存在大量的互动,互相利用。欧洲人跨越大洋,在亚洲沿海地带小心经营,来自东方的奥斯曼人则长驱直入中欧。欧亚之间不是单纯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互有攻守、征服。
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欧洲主宰了世界500年。真实的故事是,这是把欧洲后来才在国际体系中享有的中心、统治地位错置到数百年前的历史时期所产生的误解。
新的探讨总能给我们新的启迪,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杰森·沙曼以其国际关系专业的学术素养,从更高层面而非单纯站在欧洲立场上,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演变进行深入思考,其观点给人以启发。他给予东西方同样分量的关注,既是学者应持客观立场的学术要求,也是受全球史观影响使然。他试图从一个更具世界性的视角揭示军事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多样性关系,告诫人们不要从结果倒推原因,主张历史并非只有一条单行道通向唯一的命运终点,而是存在导向多种结果的不同路径。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让他的著作获得了许多学术大咖的点赞。因《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享誉学界的斯文·贝克特称赞《脆弱的征服》“将改变你对近代早期世界的看法”。
《脆弱的征服》对欧洲扩张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但书中的观点并非定论。我们应该从书中获得新的思考方法,而不必视作者的观点为真理,否则就陷入了另一种偏见。
西班牙征服者
初看之下,西班牙在16世纪初征服了美洲的大片土地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明证,证实了即使在面对难以置信的实力对比时,西方军事优势也可以成功地支撑起帝国的开拓。征服者的军队规模如此之小,处在远离家乡的陌生土地上,却不断地战胜数以万计的美洲军队,摧毁了两个帝国,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依靠奴役和种族灭绝,西班牙人获得了大量新的土地、人口和收入。军事革命论若是真的有效,那必然是在此处显现了。除了本身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之外,西班牙征服者的胜利还常常影响人们对欧洲扩张的整体看法:“哥伦布的经历超越了地理界限,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扩张的主要象征。”
只要我们对西方与地中海地区、非洲和亚洲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稍有了解,就能知道军事革命论是多么站不住脚。但是,在考察其他地区之前,还是先仔细考察美洲吧。这里我们并非要总结历史记录,而是要评估历史事实与军事革命论的相关性,并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是征服者的数量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1521年的特诺奇蒂特兰战役高潮时,科尔特斯(Cortes)带进墨西哥的士兵仅有900人,而1532年皮萨罗(Pizaro)在秘鲁时手下只有170人。他们以少胜多的战绩经常被拿来证明西方在技术或组织上占据优势,但这一事实本身恰恰排除了军事革命论作为西班牙征服的有力解释的可能性,因为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人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军队上的。如前所述,军队的规模是将军事革命论这一论点的纯军事层面与创建现代主权国家联系起来的关键。有人可能会辩称,由于西班牙人有当地盟友的帮助,最后在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击败阿兹特克人的军队人数大约有7万之多。但这些盟军与军事革命论中所说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常备职业军完全不同。
西班牙军队规模小,是因为他们像哥伦布踏上最早的探索之旅时一样,基本上都是私人力量。西班牙国王授权这些私人力量远征,条件是他们所发现的土地要归国王所有,土地上的居民要接受教会的洗礼,而开发新领土的权利在一段时间内按照一定安排(委托监护制)分配给那些用自己的资本和生命冒险参与探险的人。比如对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早期征服与殖民,“远征的资金是通过冒险家和银行家之间订立的合约来募集的,因为扩张始终是一种伴有风险的生意”。亨利·卡门(Henry Kamen)接着评论道:
西班牙没有派出一支军队参加“征服”。西班牙是通过一小群冒险家的零星努力实现其统治的,后来国王试图控制这些冒险家……多亏了委托监护制,国王能够在新大陆发起军事行动,而不需要向那里派遣军队,而事实上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能力往那里派遣军队。西班牙人在“征服”期间发起的军事行动完全依赖于私人组织。
征服事业本质上的私人性质驳斥了新大陆的胜利是由国家力量实现的观点,这里的国家力量指的是由公共财政收入供养、由王国官僚机构控制的军队。总的来说,早期的征服者甚至不是士兵,他们通常是由亲属团体招募的。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和训练指导,而这正是新式军队的基本特征。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没有军官,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正式的指挥系统。
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军事优势论的支持者可以用作论据的,那就是征服者确实拿着枪而他们的敌人没有枪这个事实了。学者们经常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所讨论的技术并不仅仅是实物,也包括组织技能,甚至可能包括使技术发挥全部效能的文化特征。然而,尽管有这样的争辩,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还是倾向于将技术默认为物质技术,尤其是火枪。与之对立的问题是,如果对技术的定义变得包罗万象,纳入组织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特征,那么这个词的含义就被拓展得超出了常识的范畴,上述解释也就不具备说服力了。这就是霍夫曼给出的定义所存在的弱点,在他给出的定义中,“技术包含很多东西,而且它是被有意规定成这样的,因为它必须囊括所有可以提高胜利概率的东西”。通过技术优势来解释胜利,再把技术优势定义为一切提高胜利概率的东西,这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
那么,在西班牙最初的征服中,技术和战术的作用是什么呢?对于军事革命论来说,这里的难点在于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军队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更接近中世纪军队而非近代军队。如上所述,他们的军队规模很小,是临时组建的,且成员不是职业军人,所以只接受过最低程度的操演和训练。虽然他们的确拥有一些长枪(火绳枪)和少量火炮,但绝大多数战斗还是近身作战。欧洲人所拥有的最大技术优势一般被认为来自征服者的钢剑和盔甲27,这两种装备在欧亚大陆上已经流行了数百年。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在击败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这两件事情上,“火枪没有冷兵器重要”。另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配备火器的西班牙人在不得不把武器换成棍棒之前,能打出一枪就算运气好了”,但是“有一件武器……效率无可置疑,那就是钢剑”。还有一位历史学家也同意“其陌生感带来的最初冲击力消失之后,火器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了”。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认为,即使西班牙人根本没有任何火器,这些远征的结局也是完全一样的,要知道西班牙人也使用了威力十足的十字弓。因此,就算是中世纪的十字军到达美洲,他们可能会像征服者一样成功。
当武器转向战术,火枪的角色被边缘化,战斗中不再有火力齐射,甚至在中世纪晚期的战争中作为主要推进力量的长矛方阵也消失了。在1559年的一本关于美洲战争的小册子中,一名征服者老兵这样解释:“在美洲,战争的样式和实践与欧洲的完全不同……线形阵列、层级化军事单位及长期驻防,被用于执行搜敌—歼灭任务的小规模隐秘作战单位所替代。”如果没有火炮,那么火炮要塞也就没有必要了;还有侧舷炮战舰,就算它们在当时已被投入使用(此类战船是在第一批西班牙舰队和葡萄牙舰队前往美洲和亚洲后才被引入的),也就与西班牙冒险家战胜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没有任何关系了。
事实上,比任何单纯的武器或者特定战斗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征服者的美洲盟友的支持。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与西班牙冒险家结盟的族群,不仅在击败阿兹特克人时提供了绝大部分军队,还提供搬运工帮助西班牙人运送补给,在西班牙的后勤支持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欧洲人的成败完全解释为后勤问题,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他们如何成功地利用原住民的支持去应对后勤上的挑战。”比如,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美洲人的帮助,建造和运输用来攻击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小船,包括挖掘运河来部署这些小船,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一种观点认为西班牙人在操纵中美洲政治时玩了一出漂亮的外交游戏,然而,罗斯·哈西格(Ross Hassig)认为不能被这种后见之明的观点牵着走。他指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西班牙人对当地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事实更接近于西班牙人实际上被他们的盟友操纵了。然而,美洲人也没有预料到疾病的全部影响,以及西班牙人最后的背叛:双方都处于一无所知的境况中。这种情况被称作“双重错估”:“文化交流的双方都假定某种形式或概念以与他们自身文化传统相近的方式运作,而对另一方的解读不了解或者没有加以重视。”因此,尽管西班牙人后来认为当地人已成为国王的忠实臣民,但后者认为统治他们的是自己的首领。
在讨论当地盟友的重要性时,霍夫曼提出了尤为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欧洲人正是靠着先进的武器才赢得了盟友的支持,就这一点来看,“与他(科尔特斯)结盟的决定实际上恰恰证明他拥有技术力量,而非证明技术无关紧要。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葡萄牙人的亚洲盟友”。对此,我可以做出两点回应。首先,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制造钢剑和盔甲是关键的技术,这两项技术虽然对于美洲人来说是新鲜的,但在欧亚大陆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这里没有任何近代因素。其次,即使军事优势可能是征服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仍然远远不如疾病和当地盟友重要。
前言与致谢——1
导论 军事革命和第一个国际体系——1
第1章 伊比利亚的征服者与恳求者——45
第2章 主权公司和东方帝国——86
第3章 同一背景下亚洲对欧洲的入侵 130
第4章 结论:欧洲人最终是如何获胜的(在他们后来失败之前)——172
注释——198
参考文献——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