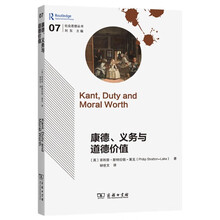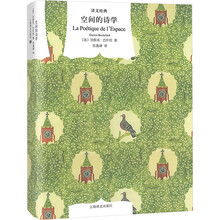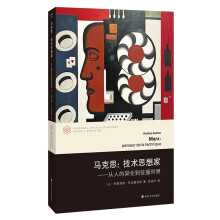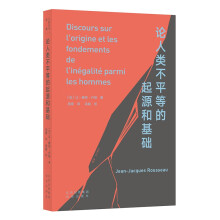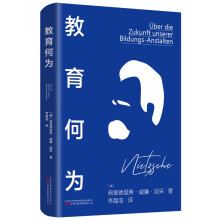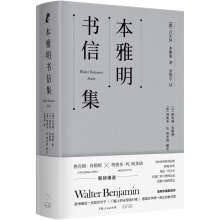一、现代政治哲学将其视野局限在对社会的解读。为了“人们征服自然以便改善其环境之故”,它放弃了认识整全的目的,用柏拉图的话说,即委身于历史世界的洞穴,囿于其居民的需求和实践问题,而放弃了人类完善性之维度,该维度包含了洞穴外部的维度。于是乎,人类孤独无依地落入现代思维的中庭。与古代的宇宙中心论特点以及中世纪的上帝中心论思想相比,现代的人本中心论这一基本特点尤为明显。为了获得安全保障,政治哲学委身服务于世俗权力。
二、限制认知兴趣并意图使实践性解决方案变为现实,且二者都以限制道德标准为前提。现代对人的理解不再是基于他能够是或应是的那样,而是来自人实际所是的那样。①古典道德的规范性要求与基督教一样,都阻碍了实践性意图,基督教通过原罪意识削弱人的地位并使人无法自主。道德标准的降低不可避免地为古典哲学的方案带来剧烈变化,并且造成德性理解上的关键变异。由于局限于历史洞穴的实践问题,德性再也不能被理解为社会所应遵循的超历史性标准,相反,社会标准成了人们本应理解为德性的事物的准绳:社会所认为正义的并且对其有利的,才是正义的。
在此观点下,德性的道德之维因市民德性之故而被取消,爱国主义、忠诚于集体性的利己转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自私自利与激情从德性之中解放出来,它们不再受到德性的制约和平衡,它们作为好胜心(Ehrgeiz)和荣誉心(Ruhmsucht)迅速成为德性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关,只要激情、自私自利以及权利诉求能够更轻易地用来在实践上实现利益,即对道德德性的呼吁、对自然秩序的适应以及对义务的履行,那么就会产生动机问题。
现代的伦理观是享乐主义的,是将善等同于舒适。其独特之处在于将享乐主义变成政治构想的根基。古典享乐主义的自我理解是非政治的,是政治社会边缘的个人态度,而社会的行之有效需要其他原则。现代的政治享乐主义则变成了一种学说,它比其他任何学说都更多地带来社会状况的激进变革。
三、政治和道德的重新定位造成的后果,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中心论的现实观反对把人理解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或者将人看作应归人创世框架之内的造物。相反,人本中心论对整全的关注选择了属人的视野,具体而言,就是作为世界建构和构造原则的属人意识这一视野。主观性正是一切丧失了自然根系的“文化”的根源。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改变有多个方面:
1.通过适应社会的配额目的,人们丧失了与自然目的的联系;
2.自然不再是属人生活持存的且需要保留的根基,反而成为必须借助文明来克服的敌对状态。现代契约论赞成一种自然状态的构思,享有基本权利、自私自利的个人在其中处于相互威胁的关系之中。自然状态着眼的是对自身的否定;
3.不仅被理解为原始相互威胁状态的属人天性,而且外部的自然,都被视为现代方案实际意图的障碍。自然和偶然都与人为敌,因而必须被征服。现代的文明方案即是对自然的反击。
四、要实现现代的方案,就需要重新定位科学,后者不应该再关心对自然的理解,相反,人们更多是把科学作为恣纵自身权力的工具。现代方案的前提是与古典科学原则彻底决裂。仅仅指出17世纪的科学拒绝终极因,以及目的论思想并非晚至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才声名狼藉,这是不够的,因为古代的唯物论者也拒绝终极因,但他们并没有强烈反对好的生活等于合乎自然的生活之说,而现代科学质疑的正是这一点。现代科学与自然为敌,与其说是基于科学一方法论的发现,毋宁说是基于道德决断。总之,自然使人难以勉力维持生命。现代运动乃基于让人通过主动进取来摆脱自然所施加的奴役这一坚定决心,它表现在号召人们征服自然。自然于是被视为仇敌,而科学则是为征服自然服务并遏制自然的武器。鉴于这种构想,人们在自然性之外探寻着阿基米德支点,因为自然性已成为非一人性的近义词。与此同时,知识的功能也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对人类自视为其组成部分的整全的冷静审视,相反却成了一种在盲目和漠然的必然王国中生产求生机制的工具。故而,霍布斯选择了一种建构主义式的(konstruktivistisch)方法,它能够在唯灵论(Spiritualismus)与唯物论(Materialismus)之间保持严格中立。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