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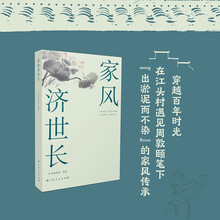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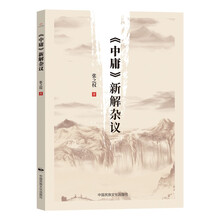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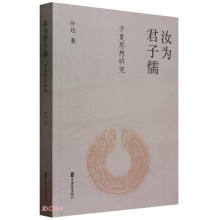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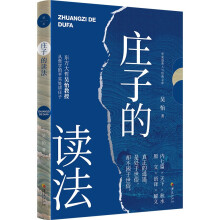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理学家是如何对《四书》进行阐释、发挥、利用的?
►不同的阐释、发挥、利用倾向对理学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有何特点、意义与作用?
►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发展对《四书》学的发展、兴盛又有何影响?
本书从思想史、学术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的角度进行论述,力图向读者展现《四书》学与理学相伴相生的发展进程以及两宋儒学的变迁发展。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汉、唐至宋,理学家朱熹将之合为一体,遂有《四书》之名。朱熹等理学家对《四书》进行编排、训释、诠解,使其逐渐具备了单篇所无法比拟的理论力量。本书系统地论述了《四书》学的渊源及在两宋时期的演变与发展,探讨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思潮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着重从经典诠释学的角度阐发了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学术成就与思想贡献,并从儒家的人文信仰、实践工夫的角度探讨了朱熹《四书》学的学术成就与思想特色,试图通过上述分析,揭示儒家思想及其知识形态的历史特质与文化特色。
朱熹的《四书》诠释: 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
以《四书》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奠定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基础:第一,他们肯定人文法则的仁、义、礼、智与超越性的“天”“天道”具有内在联系;第二,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道德理性、道德实践的途径领悟天道、参赞化育。但是,早期儒学仍然留下来一些十分重要而且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儒家人文法则的仁、义、礼、智与终极实体的“天”“天道”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就需要建构一套哲学高度的思想范畴及知识体系来解决这一问题;第二,为何通过体认内在心性的道德理性、道德实践可以通向终极关切?这就需要重新诠释先秦儒家的修身理论,建立一套可以规范操作的修身工夫,使个体能顺利实现形而上的精神体验与形而下的日用伦常的统一。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以毕生精力研究、诠释《四书》,就是希望承传早期儒学已经奠基的人文信仰,并进一步解决早期儒学在信仰建构方面的上述问题,从而真正完成儒家人文信仰。朱熹通过重新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继承、确证先秦儒学中奠定的信仰,并进一步以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与哲学化的逻辑体系,来解决人文法则与终极实体的内在联系,建立一条以道德理性、日用实践来实现终极关切的程式化途径,以真正完成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
首先,朱熹在诠释《四书》时使儒家信仰更加人文化,这体现在他努力将人文法则上升为终极实体。
《四书》所倡导的仁、义、礼、智道德法则,如何与那主宰天地的“天”建立内在联系呢?
朱熹以一个比“天”更加具有理性色彩、哲学意味的“理”来沟通二者。
一方面,他在诠释《四书》时,将孔孟倡导的仁义道德、社会礼仪以“理”来概括,他说:“次而及于身之所接,则有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所谓理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所谓“理”,就是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不得不遵循的必然法则。他在《大学或问》中又将其称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他说:“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这样,人们在日用伦常中必须遵循的仁、义、礼、智,天地万物所必然贯彻的自然法则,均成为主宰世界一切的“天理”。“天理”也因此成为日月星辰、山川草木、君臣父子、人伦日用等一切自然的、社会的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本质与法则。
另一方面,朱熹又将《四书》中的“天”“天命”也同样诠释为“理”“天理”,使那个神圣而又超越的“天”“天命”转变为更具哲学理论色彩的“理”“天理”。《孟子·梁惠王下》中“交邻国有道”章中有“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在这里所言的“天”,是对宇宙中最高主宰者的称谓,象征着那个神圣而又超越的终极实在。而朱熹则将“天”诠释为“理”,他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朱熹所诠释的“理”,是人文世界之中的“所当然之则”,是自然世界中的必然法则。故而尽管“理”仍有一种主宰力量,但它主要是一个表达宇宙世界中普遍法则的哲学概念,是构筑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
为了更进一步地从学理上论证人文法则与终极实在的联结,朱熹必须要建立一个逻辑化的宇宙论体系。《四书》对“性与天道”问题语焉不详,朱熹以《四书》中有限的资料对“性与天道”等有关信仰的重大问题重新作出创造性的诠释。《中庸》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简约的命题仅提出性与天命的关联,却无法说明人性与天命的内在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不能满足儒家人文信仰的理性化要求。而朱熹在对这段话的诠释中,融入了一个宇宙论哲学,从而使这个简约的命题具有了宇宙论体系的理论背景,故而其思想内容变得更加丰富、深刻、系统。他诠释说:
命,犹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将“天命”与“性”的关系纳入到一个大的宇宙论哲学,即从天理到阴阳五行,再到万物化生,使得世界万物均是气以成形、理以成性,这样,“天命之谓性”的命题就获得了系统的、哲学化的论证。于是,无论是礼乐刑政的外在人文,还是仁心德性的内在人文,均因其既源于宇宙的终极实体,又体现于自我的个体存在,即所谓“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从而不仅在学理上论证了人文法则与终极实体的内在联系,也为个体的人文信仰奠定了理性的基础。
朱熹以“理”来统一“天命”与“性”。但是,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天命”是代表宇宙终极实体的概念,表达的是宇宙万物本源和主宰于“一”的观念,而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各有其性,就是对于人类而言,每个人的品性也是千差万别的,故而性有万殊的差别。
如何解释天命的“一本”与事物的“万殊”之间的差异呢?
这也是朱熹必须要通过理论论证的重要问题。朱熹在诠释《四书》时,以“形而上”与“形而下”、本性的同一与气禀的差异来解释这种“一本”与“万殊”之间的关系。他在诠释《孟子》“生之谓性”章时说:“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性,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气。”他以“形而上”之性与“形而下”之气来说明“一本”的同一与“万殊”的差异及其来源,他认为“形而上”之性即是天理,它是同一的,而天地之间、人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于“气禀”。他说:“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他认为先天的“气禀”之异,是人物之间、人人之间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人性因本之于天理,故而是相同的。
朱熹在诠释《四书》时,多次论证了这种“一本”与“万殊”之间的关系。譬如,他在解《论语·里仁》中“吾道一以贯之”时说:“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朱熹本只是借理一分殊的道理,说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原因。但是这种解释正是其宇宙论哲学的重要思想,所以,他在其他多种注释中均详细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以在理论体系上解决“一本”与“万殊”之间的统一与差异。
其次,朱熹的《四书》诠释使儒家信仰日益理性化,这尤其体现在他对理性主义认识论、修身方法的倡导。
孔、孟等原始儒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如何体认天道的方法与途径,其中既包含大量直觉体悟等非理性的体认方法,也包括知识认知的理性化体认方法。由于孔、孟等儒学大师对这些理性认知的方法同样是语焉不详,更没有能够建立起体系化的理性认识论,所以,重建儒家人文信仰的朱熹迫切需要通过诠释《四书》,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认识论思想体系,从而使儒家思想的理性主义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朱熹的理性主义认识论体系,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的诠释而建构起来的,当他在诠释《论语》《孟子》《中庸》的认识方法时,亦是借用对《大学》的诠释成果而加以贯通的。所以,我们需要重点探讨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认识论思想。
朱熹建构了“性与天道”的宇宙论体系,解决了人文价值超越源头的问题,但是,应该如何体认那作为终极依据的“天理”呢?朱熹对《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学术关注。在他看来,儒学从来就有重视读书学习、研察事物以穷究万物之理的理性传统,这与佛道宗教那种倡导非理性的体悟是大不相同的。他深感《大学》一书以十分简略的方式谈到的“大学之条目”十分重要,尤其是其中的“格物致知”说更是如此。他说:
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
他有意将《大学》的“格物致知”与佛教的“‘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的认知方法对照比较,强调它们是不一样的,而儒家体认方法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读书而原其得失,应事而察其是非”的理性精神。
然而,《大学》经文只是列出格物、致知的步骤,并无具体的解释说明。这一点,既给朱熹重新诠释“格物致知”说带来了困难,也给了他更大的创造性诠释空间。朱熹提出《大学》经文本有阙漏,并对自己认定的阙漏作了补充。朱熹在所补的经文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对“格物致知”方法的认识: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这段话,比较鲜明地表达了朱熹理性主义认知方法和思想信仰的特色。一方面,他以体认宇宙的终极存在——“理”为最终的认识目标,他相信认知主体能够实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天人合一境界,这种状况显然是由他内心深处的精神信仰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他又反对那个“一超直入”的宗教信仰与体悟,而坚持认知主体的“知”与天下之物的“理”的对应性,认为只有通过“即物而穷其理”,即“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知识积累,在这种“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的过程中,逐渐实现认识的深化与拓展。朱熹进一步强调“格物”是《大学》一书的核心,认为“此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认得……本领全只在这两字上”。而“格物”经过他的诠释后,既保留了天人一理的信仰,又弘扬了儒学的理性精神。
由于朱熹的《四书》诠释坚持了这种人文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原则,从而使原始儒学奠定的人文传统得以进一步弘扬,将儒家的人文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来,早期儒学就是从西周的宗教文化、伦理文化的母胎中孕育出来的,早期儒学继承、弘扬了西周思想文化中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建立了一个更具理性精神、人文取向的仁学体系。但是,早期儒学亦部分保留了西周思想文化中的宗教观念,继续承传着最高主宰者“天”的信仰。这种既崇奉人文理性,又具有对天命信仰的思想形态,就构成了早期儒家人文观念的信仰特色,或者说是儒家思想的人文特色。
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进一步拓展、弘扬了原始儒学本有的理性精神。朱熹以知识理性的态度和哲学范畴的构架建构了以天理、太极、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取代原始儒学中的那个具有主宰力量的“天”“天命”的信仰,用格物、致知、实践、穷理等摄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来建立认知论,从而使儒学变成了一种“哲学化”的儒学。
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也弘扬了原始儒学中的人文精神,不仅使仁、义、礼、智的道德规范得到了更加系统的论证,获得了更加崇高的地位,得到了更加严格的遵循,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原本是人文法则的道德规范直接成为主宰天地世界的天理、化生天地万物的太极,当人文法则几乎代替了自然法则而上升为天理时,就真正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成为一种成熟形态的人文信仰。
总之,朱熹的代表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完成了儒家人文信仰的建构。在这部里程碑式的文化巨著中,朱熹表达出了更加强烈的人文意识与浓厚的理性精神。然而,几乎在朱熹进一步强化儒学的理性化、人文化的同时,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也同时强化了儒学的信仰,从而强化了儒学的宗教功能。可以说,在朱熹的《四书》学与宋儒的思想体系中,宗教观念的淡化与宗教功能的强化几乎是一体的。
目 录
上篇 导 论
第一章 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的研究状况
第二章 《四书》、《四书》学及汉唐四门之学流变
第一节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概况
第二节 《四书》之名的确立及《四书》学
第三节 汉唐《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门之学的渊源流变
中篇 宋代《四书》学的形成与理学体系的建构
第三章 宋代的儒学复兴活动及《四书》学的兴起
第一节 宋初社会特点及儒学的时代课题
第二节 宋代儒学的内外危机
第三节 宋初的儒学复兴活动及《四书》学的兴起
第四章 北宋《四书》学的形成与理学思想体系的初步建构
第一节 对《四书》的阐释、利用、发挥是理学思想体系建构的重要基础
第二节 从《四书》学看北宋中后期儒学诸派的分歧
第五章 湖湘学、象山学与《四书》学
第一节 湖湘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第二节 象山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下篇 宋代《四书》学的定型与理学体系的完成
第六章 朱熹《四书》学的形成过程与治学特点
第一节 朱熹《四书》学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朱熹《四书》学的治学特点
第七章 朱熹《四书》学的诠释方法
第一节 《四书》诠释的两重进路
第二节 “文献—语言”的《四书》诠释方法
第三节 “实践—体验”的《四书》诠释方法
第八章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人文信仰
第一节 《五经》时代及其信仰
第二节 《四书》:儒家人文信仰的奠基
第三节 朱熹的《四书》诠释:儒家人文信仰的完成
第四节 朱熹《四书》学中人文信仰的特征
第九章 朱熹的《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第一节 作为儒家工夫论的《四书》学
第二节 《四书》学工夫论的体系构架
第三节 圣门第一义:“行”的工夫
第四节 圣门第二义:“知”的工夫
第十章 朱熹的《四书》学与理学体系的确立
第一节 以《四书》为核心的新经典体系的理学旨趣
第二节 《四书集注》中的理学道统论
第三节 朱熹《四书》学中的天理论建构
第四节 朱熹《四书》学中的心性论建构
第五节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
附论 宋代理学《四书》学的传播与理学的社会化
第一节 理学《四书》学思想向最高统治集团的传播与渗透
第二节 理学《四书》学向士人的传播与渗透
主要参考及征引文献
初版后记
修订本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