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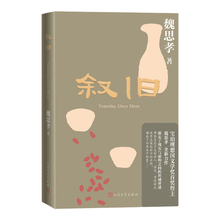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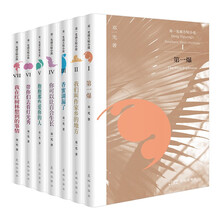




ê 解放军文艺大奖、黄河文学奖得主北乔最新短篇小说集。
ê 关于河流的十一个故事在回忆中沉潜,在想象中漂浮,在时间中化为流水,托载起故乡书写的多种可能性。
ê 以最本真的方式展开的乡村叙事,用一双孩童的目光,刺破村庄大地上的一切隐秘:欲望与人性、死亡与流年、爱与羁绊、道德与希望,在平凡的生活中交织缠绕。河流慷慨地环抱朱家湾,人们无声地拥抱命运。
ê 我们总是一遍遍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在这里,有关于生活的全部真相。正如作者所说:“已经归隐于岁月的村庄,端坐于黑暗之中,长在我的皮肤上,化在我的呼吸里。我不是村庄的全部,我的全部来自村庄。”
泡在阳光里的芦苇
1
我跟在母亲屁股后头上村顶西头的梅丫家,从我家到梅丫家是一条灰白的路,右边是绿里发黄的麦子,左边是灰绿色的芦苇,好闻的河风把芦苇和麦子都吹得不停地点头哈腰,芦苇丛中有鸟儿在歌唱,是一种像麻雀又比麻雀个头小的鸟,我们叫它芦柴儿。我捡起一块干硬的土块扔过去,一根芦苇被砸断垂下头,芦柴鸟儿又飞到另外的芦苇上去了。我快活得要死,远比后来我第一天去上学还高兴。
来的人真多,屋里、屋外的晒场到处是人。大人们三三两两地说笑,小孩儿屋前屋后乱窜,就和麦子上了村里晒场的情形一样。有人在哭,但我听不清楚。
梅丫见我来了,一蹦一跳地跑过来,笑盈盈地说:“泥巴,我奶奶死了。”
我说:“晓得,菜多吗?”
梅丫脸上有泪痕,但这不影响她那欢快的笑靥,她说:“多呢,有肉,块儿可大了,有鱼、鸡蛋,还有,还有……我说不上来,反正你吃不了。”
梅丫穿一身白衣服,头上戴一顶别着一条红布条的白帽子。她跑起来时,那红布条翻飞着动着,说话时又温顺地耷拉着。
我摇着母亲的手哀求道:“我没帽子,我还没戴过帽子呢。”这话被身后的爷爷奶奶听到了,爷爷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嘴唇翕了翕但没吭气。奶奶侧过脸看了看母亲,那眼光就像秋天的芦苇秆。母亲脸一沉怒瞪着我说:“瞎嚼蛆,掌你嘴。”说完,呼地抬起巴掌要掴。 奶奶拉住母亲举到半空的手:“你怎和小孩家计较?什么还都不懂呢。”
我趁机挣脱她的手溜进小孩儿堆里。大人们边吃边说笑,我们小孩儿一会儿上桌吃,一会儿要么在桌洞里钻来钻去,要么在外面躲猫猫相互追逐。后来,梅丫被她家大人拉去磕头,我看到梅丫奶奶躺在棺材盖上,双手埋在屁股下。她脸色白白的,像刚出笼的白馒头。她睡得真香啊,这么多人在吵,都弄不醒。
丧席吃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反正往家去时太阳都落西了。母亲问:“吃饱没?”
我搂着肚皮,说:“到明朝中午不吃都不饿。”
爷爷迈着四方步像只鸭子在灰白的小路上慢悠悠地走着,用鳖骨剔他那黄得跟玉粟①似的牙,咧开的嘴角不住地流金灿灿的口水。奶奶的小脚像踩鼓点,身后落下两排鸡蛋大的窝。
我说:“这丧席该从早到晚连吃三顿,最好从村西头挨排排吃。”
母亲说:“又瞎嚼蛆了。”
我说:“没,菜又多又好。”
我腮帮子沾满了红烧肉的酱色,嘴唇浸泡在肥油里,说玛这儿,口水又禁不住流了下来,。
母亲说:“说不好我们家也快办丧席了。”
我说:“好啊,什么时候哇?”
母亲没吭声,只是扣紧我的手,把我当成一头羊往家牵。
这时,西面天空已现出和梅丫帽上的红布条一样的颜色。芦苇在晚霞的映照下,浑身上下红通通的,落在水面、河沿上的影子也是淡红的。浸着阳光的芦苇仿佛在燃烧,发出豆荚爆裂时的噼啪声。整个河面都成了一片火海,我有点担心这样下去会把鱼烧死。我老是在这火红中望见梅丫奶奶那苍白的熟睡了的脸。
2
河围着我们这江苏东台朱家湾画了一道弯向东走了,朱家湾像戴了一顶水帽子,两岸密密长长的芦苇是帽子上的两条装饰带。芦花纷飘时,好像有数不清的蝴蝶围着帽子在跳舞。
河里有无数知名儿和不知名儿的鱼,河泛时,调皮的鱼儿会突然在我放个屁的工夫全部冒出来,水面挤满晃动的眼睛咂巴的嘴。那些鲦子、河虾之类的家伙特别起劲,像我们在村晒场中蹦跳一样在水面上跳跃,有的能飞出好远。这时用篮子捞,篮篮不会落空。人站在河沿,时不时有蹦上岸的鱼虾在脚旁打滚。我不会去捡,也不会用篮子下河捞。
P1-4
泡在阳光里的芦苇 / 001
打把杀人的刀 / 027
大宅院外的蝴蝶 / 039
打架 / 057
和鳗鱼有关或无关的故事 / 070
金色裸女 / 097
尖叫的河 / 121
香米 / 142
香稻 / 163
挑河 / 185
桥头有条狗 / 199
跋 共时空的旅程 / 215
附录 刊发索引 /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