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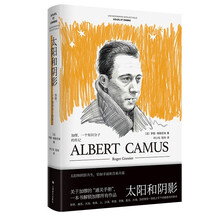

神童兰波,浪子兰波,文学超新星兰波!
兰波是个永远的谜。
为什么他会成为全世界一代代人的青春偶像?
为什么说他摧毁了几个世纪的法国诗歌传统?
如超新星一般爆发,他放弃文学、四海漂泊又是在逃避或追寻什么?
比起众多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却又解答未尽的大部头,本书
1. 仅以10万字的篇幅带你把握兰波波澜一生的主线,及其身后余响。轻而全,短而精。
2. 所引诗篇法语、汉语双语对照,从诗律角度解读兰波诗艺的颠覆意义。
3. 配图丰富,甄别细致,多幅图片在中文世界已出兰波传记中未见。
4. 作者塞思·惠登是兰波研究当代中坚,英语新版权威兰波诗文全集校订者、导读者,对兰波的解读、评述在前人基础上颇多阐发。
既然巴黎不再欢迎兰波,他就和德拉埃在夏尔维尔光顾各种酒吧。与此同时,魏尔伦回到了首都,向玛蒂尔德保证他已经和兰波分了手,说服她返回巴黎,她在3月中旬也这么做了。至少在表面上,婚姻秩序得以恢复,但是在她背后(毫无疑问也在她鼻子底下),两位诗人仍然保持着定期书信往来。5月初,兰波悄悄返回巴黎,两人故态复萌。如果说她丈夫醉醺醺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玛蒂尔德可能怀疑其中有蹊跷,那么当他回家的时候流血不止,她就该担心了。那是5月9日,据目击者夏尔·克罗称,他们在“死鼠”咖啡馆(位于皮加勒广场)喝酒时,兰波在玩一把刀,突然将它刺进了魏尔伦的手和腿。刀这一话题在6月还会出现,喝醉了的魏尔伦在一家餐馆里拿着刀威胁玛蒂尔德(前一天晚上,他还试图烧她的头发)。同月,兰波在一封给德拉埃的信中描述了他最喜欢的消遣,信写自“巴谢特”(Parshit),日期为“约在6月”(June-ish):他高喊“尽管侍者脾气暴躁,但苦艾酒俱乐部万岁”,并描述了他夜间的写作节奏和白天喝酒取乐一样有规律(OC,368)。
尽管他的作息时间非常散漫,但是兰波专心创作的时候还是写下了许多诗歌,它们通常被称为《最后的诗》,因为那是他写下的最后的韵诗:《泪》《加西河》《渴的喜剧》《晨思》《耐心的节日》(最初名为《五月的旗帜》)《高塔之歌》《永恒》《黄金时代》《新婚夫妇》《她是埃及舞女?……》《花坛……》《饥饿的节日》《噢,季节,噢,城堡……》《记忆》《你听,四月里……》《羞耻》《米歇尔和克利斯蒂娜》《怕什么》和《乌鸦》。
模仿诅咒派的作品所表现出的轻蔑(例如向梅拉的诗集《偶像》致敬的那首十四行诗)有了更多的讥讽对象,这次是韵诗。与刺伤魏尔伦时酒徒的鲁莽不同,在这里,他如外科医生一般精准地切开了亚历山大体诗句,在这一点上十六行诗《泪》(Larmes,OC,207)就是一例。诗中的主体拙于刻画事物——j’eusse été mauvaise enseigne d’auberge(我只会是小客栈的一块破招牌),与此呼应的,是不做区分的泪水、酒和河水等液体,所有这些都使这首诗的情感框架更加复杂,因为一系列近似和故意的接近失误颠倒了含义和押韵。兰波在认可规则的同时又轻视规则。声音的重复贯穿这首诗的四个小节,全诗充满了loin(远)和 eau(水)等词中的wa和o的元音谐音以及它们在oiseaux(鸟)一词中的组合,产生了铿锵的韵律,将声音的重要性从句尾或停顿之前的传统位置中分离出来。由于没有了常规的停顿,所以后一个选择变得更加复杂:这些诗行只包含十一个音节,因此不能分为两半。《记忆》(Mémoire,OC,234—235)是这一阶段又一首韵律被撕碎了的诗,诗中留存的亚历山大体的最后痕迹被捶击得体无完肤,无法辨认。这是一首抹去韵律的诗,是在废墟上纪念韵律的辉煌过去。在《晨思》(Bonne pensée du matin,OC,202)中,诗律在被清除的那一刻获得展示,宿醉醒来的清晨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完美,因为诗歌先以三行八音节诗句接一行六音节诗句这样的小节开始——甚至以清晰的时间标记做了预告quatre heures du matin,l’été(夏季,凌晨四点)——很快就变得缺乏秩序和节奏,笨拙地、踉踉跄跄地穿过诗行,破坏了诗歌的韵律。一般情况下应该读作十个音节的诗行必须以走捷径的形式,利用单词之间的省音和其他非常规的做法来发音。诗歌开头给出的确切时间其实带有欺骗性,因为其余的诗行在八、九、十个音节之间摇摆不定,没有任何可辨别的模式。兰波单刀直入地探究这样的问题:读诗意味着什么,什么内部规律应该支配我们的诗歌体验。最后,他变本加厉,彻底颠覆了诗歌的最后一节:第五节也是最后一节以较短的第一行开始,然后才是较长的诗行。之后,仿佛在取笑这首诗本身,也许是取笑读者,兰波突然用一句亚历山大体诗行En attendant le bain [+] dans la mer à midi(当他们等待正午大海的沐浴)鼓吹一种即使是最守旧的诗人也会额手称庆的秩序。这种完美的和谐与对称蕴含着讽刺,因为——正如兰波在多个层面上所知道的——已经无家可归:诗歌已经挣脱了韵律的桎梏,任何企图羁縻它的尝试都是不合时宜的。
魏尔伦越来越把巴黎的婚姻生活看成过往烟云。他和兰波脚底抹油,前往布鲁塞尔,这座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躲避第二帝国审查员和巴黎保守主义的避风港。1862年,出版商奥古斯特·布雷-马拉西斯(Auguste Poulet-Malassis)逃往布鲁塞尔以躲避债权人;在那里,他出版了好几部诗集,包括波德莱尔写的放荡淫靡的诗。1867年,他推出了五首魏尔伦歌颂性爱的十四行诗,题为《情人们》,在书名页上,魏尔伦署名“被开除的帕勃罗·德·赫拉格尼兹(Pablo de Herlagnez)”。与魏尔伦和玛蒂尔德和解之后两位诗人仍一直保持着秘密往来同出一辙,这一次魏尔伦也在兰波不知情的情况下写信给玛蒂尔德。后来,在回忆录中,她凭记忆引用了其中一封——“我可怜的玛蒂尔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我做着一个噩梦,我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声称魏尔伦要她带上他的个人物品,因为当他和兰波从巴黎溜出来时,他只带了手杖和帽子。机不可失,玛蒂尔德和魏尔伦的母亲一起去了布鲁塞尔,试图让他永远离开兰波。她的恳求似乎奏效了:魏尔伦与这两位女性一起登上了一列开往巴黎的火车。应该说,玛蒂尔德的恳求很快失效了:兰波偷偷地登上了同一列火车,在越过边界进入法国之前为了通关而停车的时候,他说服魏尔伦改变了主意。两位诗人再次前往布鲁塞尔,玛蒂尔德只好返回巴黎,10月初她正式要求合法分居,声称丈夫和兰波之间的关系“不干不净”。
正是基于上述这几个月的事件,某位隆巴(Lombard)警官(他受命监视两位诗人)写下了他的报告。尽管有一些错误,但“罗贝尔·魏尔伦(Robert Verlaine)”和“雷姆博(Raimbaud)”的故事(还有“夏尔·德·西夫里”客串出演)还是精彩纷呈:
以下这一幕发生在布鲁塞尔。
巴那斯诗人罗贝尔·魏尔伦与作曲家兼钢琴家西夫里的妹妹结婚已有三四个月,西夫里在巴黎公社后曾被关押在萨道里,然后被运走、释放。
他们是在去年年初或年中结婚的。
尽管魏尔伦有时犯傻(他的脑子很久前就脱轨了),总的说来这对夫妻还算和谐。不幸的是,一个来自夏尔维尔的男孩雷姆博独自一人到了巴黎,向巴那斯诗人们展示自己的作品。就道德和才华而言,这位15至16岁的雷姆博过去和现在都是妖孽。
他的作诗技巧无人匹敌,只不过他的作品绝对令人费解、反感。魏尔伦爱上了雷姆博,后者和他一样热情澎湃。他们去比利时品尝了内心的安宁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
引文与英译说明
引子
1 城墙
2 田野
3 首都
4 城市
5 创伤
6 世界
7 来世
注释
精选参考书目
致谢
图片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