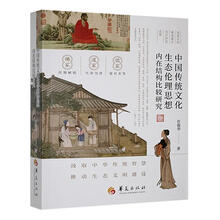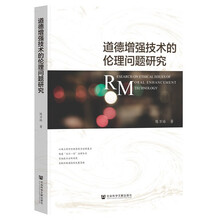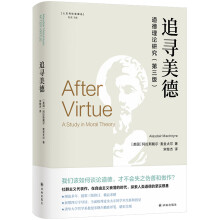生命医学伦理
Biomedical Ethics
人性是设计的对象?*
阿尔弗雷德 诺德曼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闫雪枫 译
摘要:有关技术发展对人性的影响的讨论大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立场认为技术不可能改变人性,因为人性是固定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人类通过技术创造了世界,生活在世界中的人类同样也会随之改变;还有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则认为,人类不仅能够使用技术制造自身,甚至能够有目的地设计人性。在对上述三种观点进行分析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由于技术本身尚不完善,我们无法有目的地对人性进行设计,更不应该以设计人性为目的追求人类增强计划。s
关键词:人类增强,技术,人性,进化
人类增强并非一个新兴的话题。实际上,人类增强的愿景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断引发着关注(Coenen et al.,2010)。然而,由于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共同资助的报告《提升人类表现的会聚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Converging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and Cognitive Science)的出现,有关人类增强的讨论呈现出了一种复兴的热情。NBIC代表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生物技术(biotechnolog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及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其思想是所有这些不同的新兴技术或新科技将会聚或融合在一起。这种会聚的目标之一(或许也是其主要旨趣所在),就是从认知、身体以及感知能力等方面提高人类表现。我的目的既不是批判作为研究愿景的人类增强,也不是论述增强人类是件好事还是坏事。相反,我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去谈论它。
这种质疑始于许多年前,我的主要论证之一始终关注这样一个基本的悖论:在开始讨论人类增强并证明我们拥有批判精神之前,我们必须毫不怀疑地相信人类增强在技术上的可行性(Nordmann,2007)。确实,相信这种图景并以假想的方式接受它是一种有问题的举动。在某些方面,假设这一技术项目能够克服诸多科学障碍似乎为时过早。而在另一方面,这甚至不是*终克服障碍的问题——鉴于我们现有的*佳理论,人性似乎没有可能成为设计的对象。回顾有关技术发展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改变人性的三种不同态度或基本立场将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第一种立场认为,人性是固定且不可改变的。根据这种观点,人性是一种规范性的人类本质,并且因此不能被技术改变。这种人性在整个历史中被认为是“人类学常数”,我不会否认在某些规范性方面为人性的不变性辩护是可能的。尤尔根 哈贝马斯通常被认为是这种立场中的一员(Habermas,2001)。正如哈贝马斯那样,我将回到伊曼努尔 康德给出的一种更大的启蒙定义中去。康德认为,人类从定义上就被赋予了理性的特殊能力,他们是“有理性的人”(vernunftbegabte wesen)。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尊严需要得到尊重的原因是我们有可能冒着与自身本性相冲突的风险来允许理性在每个个体中发展,就像它在全人类中所做的那样。人类进步和人性(humanity)的整个逻辑依据都与我们的个体本性相关,只有通过这种理性在每个个体当中的发展,人类启蒙才能前进。正是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承认其他人是有价值、有尊严的。持有这种观点的哲学家相信,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技术条件的变化改变这样一种与法律相绑定的人性概念。
然而,那些谈论技术改变人性或增强人类表现的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理解着人性。他们甚至可能会赞同哈贝马斯和康德,但也强调他们所讨论的人性并非规范性意义上的,而是关注一些身体特性和认知能力。然而,即使对于这种普遍且具有规范性的概念,我们也可以合理地质疑人性是否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在康德所处的时代,甚至可能对于康德本人而言,并非所有人都是真正平等的。例如,对于启蒙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女性在她们实践并发展理性能力方面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是一个大问题。同样地,当我们审视“文明”的不同等级时,启蒙思想家倾向于认为只有那些能参与文学公共讨论的人才有资格被认为是完全的人类,也就是那些能够为一般读者写作的人。换句话说,在印刷书籍和刊物的年代,是否具有使用某些技术或阅读和写作这种文化技术能力决定了一些人是否能被看作负责任和有理性的人。因此,技术甚至能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调整一般被认为不可改变的规范性定义。当然,论证一种本质的、不可变的人性对于讨论的帮助值得怀疑。
大多数研究技术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会从相反方面论证人类在创造和重新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并重新创造人类自身——对世界的重新创造当然是一个正在进行的项目。这里出现了第二种态度:我们创造了所处的世界,我们在创造新技术的过程中也创造了第二种自然。我们的世界随着时间变化,不可避免地,世界中的居民也会随着时间在重要的方面发生改变。从一种技术的观点来看,这种立场可能是许多科学史和人类学史中老生常谈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性确实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变,但并不是以一种有计划有控制的形式进行。人性的改变不是技术发展的目的或手段,它只是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发生。当我们创造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也创造了人与人之间新的交往,人与物之间新的互动,以及世界的新的特征。我们创造了获取和发展知识与数据,以及经验或感知的新模式。换言之,人类的取向和自我理解随着他们创造的世界而发生各种变化。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诸如平均寿命预期和我们的感觉器官的发展等内容是否属于人性,但它们确实是我们如何具身为人类、如何在现代世界中被构建的重要方面。举例来说,当我们阅读米歇尔 福柯和菲利普 阿利埃斯的时候,对于童年和成年的整个观念都通过技术发生了相当的改变,对于生育和父母身份的观念也是如此。例如,成为一名家长意味着什么随着生殖技术和遗传筛查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从前不存在的选择可得性发生了变化(Katz Rothman,1994)。此外,人们总是说每个人都会死,死亡是人性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的,确实如此,而且死亡很可能是人类存在中一个固定的方面。但死亡的观点真正意味着什么,以及人类事实上是如何死亡的,与技术的变化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联系。
许多例子都说明当我们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时候,我们也创造了世界中新的人类居民,人性以及我们的社会生活都以某种方式随着技术一同发生了变化。我相信我们能够超越这一被广泛共享的见解向前一步,但或许并不像一些人走得那么远。他们对于技术和人性的第三种立场或视角——同时也是*激进的一种立场,认为我们在制造我们生活世界的同时制造了我们自身,而既然我们可以制造,我们就可以设计。一直以来我们不经意间甚至以相当随意的方式做的事情,也可以以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方式进行。提出不经意做的事情可以在被精心策划之后做出似乎是一小步,但它实际上是如此巨大的一步,以至于我们不能将其采纳。它是需要被论证的巨大一步,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环顾四周,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东西都是人类决定和技术干预的产物。那么,坚持认为我们一直随意做的事情不能被有目的地做出来是出于怎样的理由?这样的理由存在吗?
一些例子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它们展现了一种设计师式的或想象的态度,并且暗示有一个人就在那里等待被设计。当思考认知增强时,想象的是在大脑中植入一个记忆芯片来凭借这种记忆装置扩展人类精神的能力。其他推测则会认为脑机接口能让我们仅凭思想来控制装置。可以肯定的是,与此类似的观点是难以解释的,甚至一些所谓的原理论证都经不起仔细的审查t。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现在不可行的在未来仍然是可能的。身体增强也是如此,有人可能会认为获得某些身体特性,如夜视或者更长的预期寿命对我们来说是可欲求的,甚至是一种义务。这种主张背后的观点是,人类或任何物种都不过是特性的一种具体集合,并且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某些特性来设计人性并控制进化的方向。这种把人仅仅视作孤立的特性的集合或总和的假设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但从这种假设出发,至少通过改变某些特性在效果上能够实现对人类新类型的设计似乎是合理的。或许有人会问,这不正是繁殖者为了培育动物的单一特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