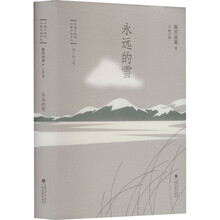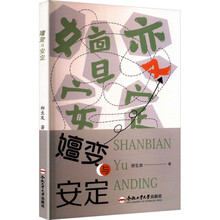从很小的时候起,大概五六岁的样子,我就知道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个作家。大约在十七到二十四岁这段时间里,我曾试图打消这个念头,但也意识到这么做是在违背自己的天性,觉得早晚我还是得安分下来著书写作。
三个孩子中我排行老二,老大和老三都与我相差五岁。八岁以前,我很少见到父亲。因为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那时我有些孤僻,很快我的言谈举止就不招人喜欢,在学校里变得很不合群。像其他孤僻的孩子一样,我总是编造各种故事,同臆想出来的人对话,我想从一开始,我的文学志向就同这种孤独寂寞以及受人冷落的感觉交织在了一起。我自知有驾驭文字的才能,有直面一切令人不快事实的能力,我觉得这为我创造了一片私人天地,每当面对生活中的失败时,我能在这片天地里得到宽慰。然而,我整个童年以及少年时期认认真真的或者说煞有介事的创作,加起来也不过寥寥五六页罢了。大概四五岁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写诗,母亲把它抄录了下来。诗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写得是关于一只老虎以及它“椅子般的牙齿”——这个词造得倒还不赖。不过我认为这首诗有抄袭布莱克的《老虎,老虎》之嫌。十一岁时,一战(1914-1918)爆发,我写了一首爱国诗歌,登上了当地的报纸。两年后,我另一首悼念基钦纳逝世的诗也在该报上发表。稍大一些后,我便不时用乔治亚风格来写一些蹩脚且通常是没有完成的“自然诗”。我也曾两次尝试写短篇小说,不过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这些便是那些年里我一本正经写下来的全部作品。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年间我确实从事过一些文学活动。首先要说的就是那些应付差事的写作,这些东西我写起来毫不费力、得心应手,但却不能汲乐其中。除了学校的功课外,我还写过一些应景诗,现在来看,当时创作这种半喜剧性诗歌的速度连我自己都觉得震惊——十四岁时,大概只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就模仿阿里斯多芬写了一整部押韵诗剧——此外,我还参与校刊的编辑工作,有印刷版的,也有手抄版的。这些校刊上都是你能想象出的最粗浅滑稽的文字,编辑起来毫不费力,就是现在我花在最没有价值报刊上的心思也要比它多。但在从事这些工作的同时,有大约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我还一直进行着另一项不同的文学练习:那是一部仅存在于我内心的日记,里面演绎着以我为主角的连续“故事”。我相信一般孩童和青少年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很小的时候,我就常常把自己想象成惊险刺激的冒险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如罗宾逊似的绿林豪杰。但很快,我便不再沉溺于这种纯粹自我陶醉的“故事”中了,转而只是对我所做所见之事作客观的描述。有时候一连好几分钟,我的脑海里会出现诸如这样的句子:“他推门进了房间,一缕金黄色的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斜照在桌面上,上面有一个半开的火柴盒,平躺在墨水瓶旁边。他右手插在口袋里,径直走向了窗边,窗外大街上,一只花斑猫正在追逐一片枯叶”。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我大概二十五岁的时候,正好贯穿了我还未从事文学创作的那几年。尽管我不得不搜肠刮肚,而且也的确费尽心思去推敲斟酌合适的字眼,这种几近刻意的情景描述几乎已是不由自主,仿佛是由于来自外界的压力而导致的。不同时期我曾仰慕过不同的作家,我想我的“故事”一定反映了他们迥然各异的风格,但我记得,它总是秉承了相同的细致描述的特点。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