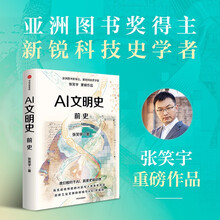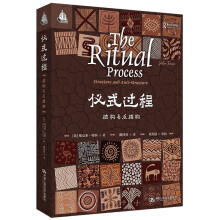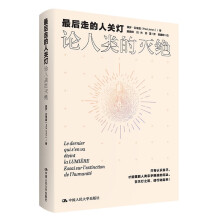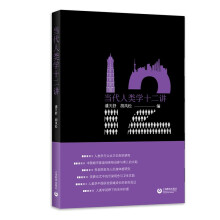关于对象的那些概念,常常使人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用创制的想象力)所造成的某个形象置于它们之下。当人们读到或听说一位在才能、贡献或地位方面是伟大的人物的生平事迹时,通常就被诱使着在想象力中给他一个壮观的外表,相反,对于一个被描述为性格细腻温柔的人则给他一个小巧玲珑的形象。如果一个根据传说的事迹而想象出来的英雄被证明是一个矮子,或者相反,如果细腻温柔的休谟被指出是一个壮汉,那么这不但对乡下人,就连对一个有足够阅历的人来说也是可惊的事。所以,由于想象力自然而然地就有走向极端的倾向,人们哪怕是对事物的期望也切不可提得很高,因为现实总是比用来实现它的理念模型要更加局限。
要把一个人引进一个社交圈子,先对他作许多高度的评价,这对他是很不利的。毋宁说,这往往可能是某个爱开玩笑的人使他成为笑料的恶作剧。因为想象力把被期待的事情的观念拾得太高,只会使这个被称道的人物在与先人为主的理念相比较时受到损害。这正是人们用夸大其辞的夸奖来预告一本书、一出戏或别的算得上是美妙的东西时所发生的事。因为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只会遭到贬低。甚至读了一出好戏的剧本就足以在看它演出时削弱对它的印象。但如果先前的夸奖与紧张期待的结果正相反对,此外又没有什么害处,那么这个对象的出现就引起最强烈的哄堂大笑。
处于运动之中变化不居的、没有自身能引起人注目的固有意义的那些形象,诸如一堆炉火的闪动的火光,各种东西的旋转,一条小溪在石174头上激起的飞沫,等等,都以大量(与当下的视觉方式)完全不同方式的观念,即内心游戏和陷入沉思所产生的观念,而维持着想象力。甚至给音乐外行听音乐也能把一个诗人或哲学家置于一种情绪,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职业或爱好去捕捉思绪,并使这些思绪能被把握,这是他独自呆坐在他的房间里不可能如此幸运地取得的。这种现象看来是因为:那本身完全不能引起任何注意的各种各样的事物,当它把感官的注意力从某个更强烈地触及感官的对象中引开时,思想就不单是变得轻松,而且也变得活跃了。这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更加紧张更加持久的想象力,来把感性材料置于其知性观念之下的缘故。英国的《旁观者》杂志谈及这样一位律师,说他习惯于在辩护时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细绳,不停地在手指上绕来绕去。这时,他对方的一位爱开玩笑的律师偷偷地从他口袋里把细绳抽掉了,于是他就完全陷入窘态而语无伦次了。因此人们说他“失去了说话的线索”。固定在一种感觉上的感官(由于习惯)而不让注意力放在另外的、不熟悉的感觉上,因而也就不会分散注意力,但想象力同时却可以更好地保持其合乎规则的活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