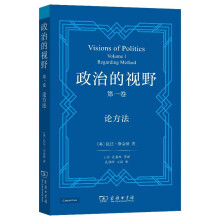《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
德意志文化的起源不在于腓特烈大帝②的一场场胜利,而在于耶拿的惨败③。腓特烈大帝在18世纪的统治是像拿破仑一样的个人统治,然而19世纪的普鲁士,无论有何种伪装,其背后是参谋军官、官僚、教授等知识专家的寡头统治。一意孤行的组织者腓特烈只擢升管理人,结果,他死后留下的普鲁士,只是一台将要在耶拿战场被击碎的机器。
就在耶拿之战的那个冬天,它仍在法国的占领之下,哲学家费希特赴柏林讲学⑤。那时的普鲁士首都还没有大学,而那些演讲也不是给青年学生,而是给这个国家最成熟的头脑,他们都处于深重危机的焦虑之中。在德国大学都沉浸于抽象知识和艺术崇拜的时代,费希特教授了爱国主义哲学。在接下来几年间,从1806年到1813年,军队、官僚和学校之间,亦即政府需要和教育目的之间,建立起了紧密联系,这构成了普鲁士制度的实质和异乎寻常的力量。在英国的1870年《教育法案》两代人以前,普鲁士就做出创举,将全民义务兵役制与全民义务教育相互联结;教授人才卓著的柏林大学,是作为总参谋部的姊妹机构建立起来的。因此,知识不再主要因其本身而被追求,而是作为通向一个终极目的的手段,这终极目的正是一个经历了痛苦灾难的国家之崛起。它是一个兵营国家,而且处在平原中央,没有西班牙、法国或者不列颠那样的天然屏障。目的决定手段,既然普鲁士的目的是那种必然以严酷纪律为基础的军事力量,其手段就不可避免的是唯物主义。从柏林的立场评判,给整个民族的知识阶层灌输德意志文化,或称“战略观念”,是绝妙的事,但从大的文明立场来看,这是给予一个国家毁灭性的动量,毁灭性是说,长远来看,要么毁灭文明要么毁灭这个国家。
过去我们一直把德国的军事地图当作一种笑谈。然而,或许可以质疑的是,不列颠和美国的大部分人是否充分意识到,在过去三代人间,地图在德国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地图是德意志文化的基本工具,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地理学家,而英美人达到此种程度的却极少。他所被教会的,不仅是在地图上识别由几纸条约所确立的传统疆界,而且是永久的确实的机会,亦即文字意义上的“手段和方法”。日耳曼的“现实政治”,存在于日耳曼头脑中的一张精神地图之上。德国高中和大学中严肃的地理教育,始于德意志文化滥觞之际。它在耶拿战役之后的一代被组织起来,主要得力于四个人 亚历山大·冯·洪保①、伯格豪斯②、卡尔·李特尔③和斯提勒④,他们都从属于新成立的柏林大学,以及此后声名远播的哥达的佩尔特斯地图出版社( Perthesof Gotha)。时至今日,即使本国有了两三家杰出的地图出版社所做的一切,如果想要一份精确生动地绘出基本地理形势的好地图,你仍须时常求助于一份德国原版。原因是德国有许多制图师都是学者型的地理学家,而不仅仅是测量员或绘图员。他们得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广阔的受过教育的公众群体,他们能够欣赏和购买绘制精良的地图⑤。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