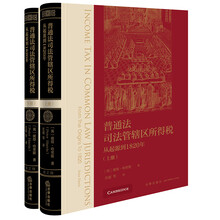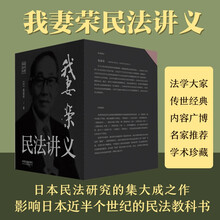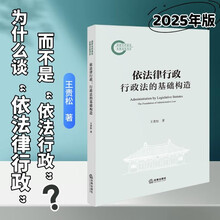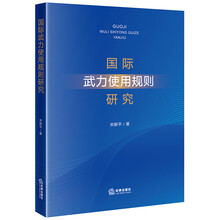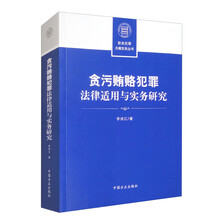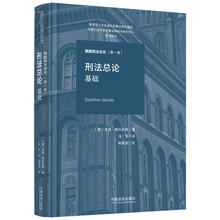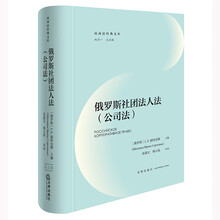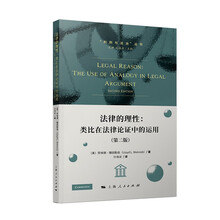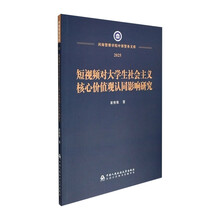《美国驻华法院研究(1906-1943)》:
在此基础之上,后继者更为关注此事。这也促成美国国会重新考虑在华领事法庭的实际运作问题,以及这一司法机构是否能在直观意义上重现美国法治形象及法治运作程序,进而达到以此规训或者驯化法治落后国的清政府,最终达致推行法律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此种意义上讲,法律帝国主义所希冀的并非仅仅在于简单意义上对在华美国人士的保护,更为突出地表达出美国作为法治国家的法治理念的宣扬。此种夙愿在19世纪中期以领事法庭模式来实践显然并不能成效立显,甚至可以说,领事法庭的司法实践所暴露的重大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与破坏了法律帝国主义这一理念的贯彻。就领事而言,他们所期盼的无不在于将其主要职责限定于商事及外交方面,因对司法案件的不当处理多令其心存畏惧;而且,重大案件中的领事常常在担任案件主审法官的同时还充任治安官,需要现场勘察、调查取证,同时又担负着地区检察官提起公诉的职责,这些行为既非领事所愿,更与美国司法独立的法治精神相抵牾;作为审判原则的领事法庭章程,既不足以维系正常司法审判,又多存在着与美国宪法相背离之规定。凡此种种,皆阻碍了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真正实践,也与伸张其程序至上的法治模式的最初目标背道而驰。此种司法图景下,亟须对领事法庭的司法实践模式作以整饬。
此种意义上美国驻华法院的创设,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领事压力,使其专注于商业事务,另一方面对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完善起到积极作用,使得在华美国商人受到专业司法人员的管辖,其纠纷得到专业化解决。诚如威罗贝所言,“如果并未触及治外法权体系本质,国会的努力至少部分地修正了这一体系中并非根深蒂固的弊端。”①这些可纠正的弊端包括各领事法庭实践与准则上的分歧;上述法庭由不习法律的官员主持;上诉至驻北京的公使以及加州地区巡回法院。由此,美国驻华法院的设置正体现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不再拘泥于旧有的制度模式,而是开始尝试一种新模式。显然,对于这一议案的倡导者丹比而言,所秉承的正是通过这一史无前例的法院机构的设置将西方司法模式适用于中国,不仅在于保护其本国在华人士的切身利益,进一步谋取美国在华经济利益,还在于向清廷彰显西方法治原则与东方法治独裁模式的截然区别。与此同时,通过此种司法机构的设置,职业法官审断程序与审判结果更为真切地为国人所知悉,更易于将此种西方司法程序与法治理念推演开来。
不过,前述理念可能仅代表着美方的一孔之见、一厢情愿,对该法院的创设,国人态度并不乐观。《东方杂志》评论道:“此裁判所较英国在上海旧有之裁判所其效力之轻重虽未可据知,然既为离于领事裁判而为纯然独立之法院,则其视英国高等法院性质固毫发无异。而其侵害中国主权者亦正相同,此诚未可忽视也。夫以上海租界而言,不过赁与各国之居留地,不能与新嘉坡、斐律宾并论。彰彰明也,此国之主权一刻犹存则彼国之主权一刻不容侵入,固无疑也。而英美国两国乃先后以其司法活动之主权移而殖于此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籍日英国高等法院其构成已历年所,今欲一旦争令裁撤,固未易期。而美国裁判所之设方始……公平交涉,度美虽强未有不可以理喻者。夫美国之建设上海裁判所其必执英国前例以为口实。”可见,对于美国驻华法院的设立,国人并未给予丝毫肯定。且在比较英美两国所设法院时,认为英国所设法院“非漫然出之,而实以条约为依据”,①言语间虽未有褒扬,却并未言辞批评,而是指出其情有可原。言外之意在于,认为美国所设法院并无条约规定,当然不可效仿英国体制设立法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