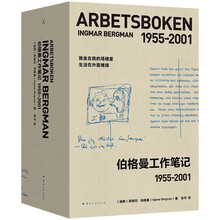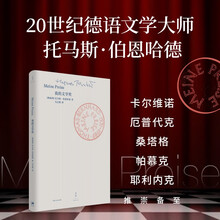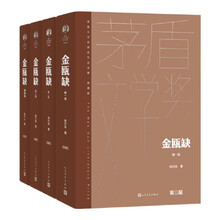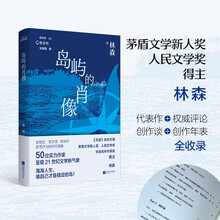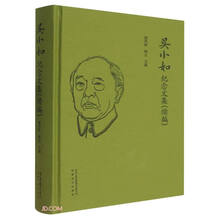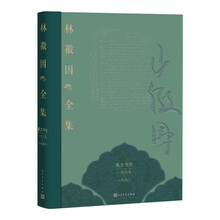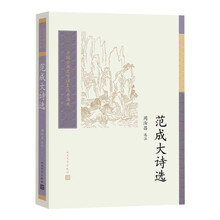《一年谈话今宵多》:
后来,读得多了,看得多了,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阶段,大体上在1994年至1999年。在这里,我与传统相遭遇,又观照以现实的眼光,自觉地疏离古典的历史感,淡化借鉴意识,而着力于探索社会人生,关注人的命运、世事沧桑,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无常感,或者说,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我曾围绕着宋、金的兴衰嬗变,以它们的都城为背景,写了一组以揭示文化悖论为主旨的散文随笔。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吟咏着前人“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诗句,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最后末帝赵爵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干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这里有历史的规律,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北宋王朝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佚,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寻索。
我还在另一篇散文里,写了原本落后的女真族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强大军事对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元朝、清朝一样,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加速了发展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愿望背反。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逐渐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优势,新的文明最后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尽管这类散文从意蕴上看,较比那些山水游记显得深刻了,但我还想继续向新的领域探索。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当时的创作心态,从我在《何处是归程》的题记中可以洞察一二。那是一首小诗:“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就是想在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现实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
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实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一向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说明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