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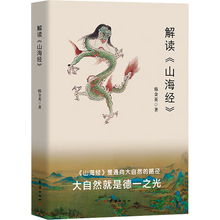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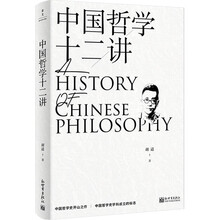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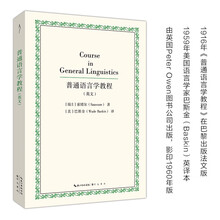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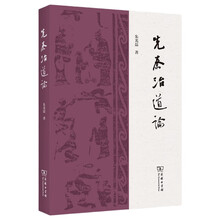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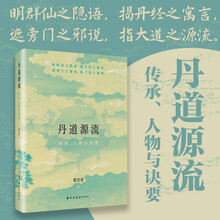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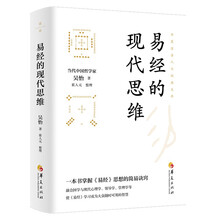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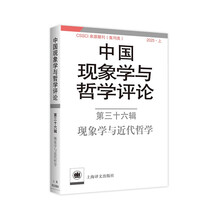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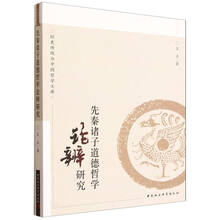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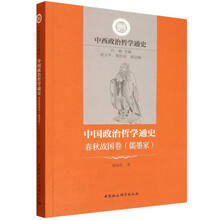
中国人哲学之第一原则
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如果中国人为人的行为规定了什么,或者为德性与道德之践行确立了什么,那么只可能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些与人心之自然是相一致的。因此毫不奇怪,他们付出的努力都换来了成功,因为他们不做任何有悖自然之事。但凡深入钻研道德事物的人,都能完全认识和观察到:即便人的诸种行为都与律法相符合,但它们各自的动机却仍是各种各样的。
诸懿行之区别与诸德性种类之区别
无疑,心灵要么对由行为引起的人内在及外在状态之变化进行表象;心灵要么将最高神意的诸属性、预见、甚至其权威作为行为动机;最后,或者是由神启示的、缺乏自然明证性的诸真理给出动机,这些真理就是关于人类拯救者基督的诸真理,也即那些被我们认作是我们宗教之基础的真理。那些从行为结果来评价行为的人们,完全以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们所养成的德性全凭自然之力(51)。而那些完全依靠理性之光来对上帝之属性和神意之预见进行思索的人们,以该思索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他们的德性则源自自然宗教(52)。最后,那些通过由上帝启示的、缺乏自然明证性的诸真理而做出行为的人们,他们的德性则有赖于神恩之力(53)。
注释(51)—(53)
(51)那种通过由自然之光所认识的内在道德性而让行为与自然法相适的“品质”(habitum),我称之为“哲学德性”(virtutem philosophicam)。然而,哲学德性只是第一种程度的德性:正如哲学虔敬(pietas philosophica)和神学德性(virtus theologica)所证实的那样。
(52)那种通过由(仅借理性之光认识的)神圣属性和神意预见(providentia Numinis)所激发的动机而让行为与自然法相适的“品质”,我习惯称之为“哲学虔敬”。当哲学虔敬与哲学德性相结合时,德性之程度便得到提升,正如我在《伦理学》第673节中展示过的。
(53)那种通过由神圣启示真理引发的动机而让行为与自然法和神圣意志(voluntati divinae)相适的“品质”,我称之为“神学德性”或“基督教德性”。因为我们对神意启示的真理所给予的认肯不是自然之功,而是神恩之功(见注释43);因此,当我们将这些真理作为动机运用在我们的行为上时,我们就不能将“认肯”算作自然之力的作用,而应算作是神恩的作用。因而,基督教德性也被神学家正确地称为由圣灵之功产生的功效:人类离开圣灵之功便无法追求这一德性。此外还需注意,在诸启示真理中,不仅有针对拯救之功和救赎计划的真理,也有可通过理性之光认识的真理,也即关于上帝及其属性、创世和保存的真理,甚至还有关于自然可恶性和可赞性的真理:神学家称它们为“混合真理”(veritates mixtas),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叫做“混合信条”(articulos mixtos),因为它们既可借理性之光、也可借启示之光得到认识。当一个通过神恩重生之人凭神圣信仰所坚定相信的东西,与一个基督社团(coetum Christi)之外的人通过自然之光所追求的东西一样,那么即使二者有着相同的动机,二者间也存在着很大区别。因为由神恩而来的认肯要强于(firmior)由自然之光获取的认肯。一个更强的认肯可产生更强的动机,而更强的动机则产生更强的愿力(propositum),从而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偏离认肯。无疑,如果有人凭神圣信仰坚定地认为,比如酗酒——如使徒强调过的——会导致一种无序的生活;那么他就会注意到酗酒之恶的内在可恶性,并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酗酒,因为他极为确定地相信,如果酗酒在某些情况下是允许的话,那个受神意启发之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然而,如果有人借自然之光认识到不可酗酒,那么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可能会相信,酗酒并不会破坏有序的生活、或者他能够避免这样的破坏。因而,即便二者具有相同的、由行为之内在可恶性产生的动机,但一个只具有自然之力以追求哲学德性、或神学家所说的世俗正义的人就会做下恶(vitio),而一个有神恩之力相助的人就能抵御这一恶。在哲学虔敬和神学或基督教德性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因为尽管二者的动机都可以由神圣属性和神意预见之功在自然之国(in regno naturae)产生,但是由于这两种德性在认肯方式上的差异,它们具有的强度(firmitatem)就不是一样的。因此,即便哲学虔敬和哲学德性在最大程度上相结合,然而信基督的重生之人的德性,和在基督社团之外了此一生、或虽在基督徒社团生活但却未达神恩之人的德性,这两种德性(译者:即哲学虔敬和基督教德性)也绝然是不一样的,而且二者间存在着很大、甚至最大程度的差别——即便是当(尽管这实际上不可能发生)信基督之人仅仅运用另一个信自然宗教之人所运用的动机。既然对神恩的认肯不是自然之功,而是神恩之功,那么一个重生之人的行为也就不是自然之功,而是通过圣灵才产生的——即便当我们假设,他运用另一个借自然宗教来调和行为与外在自然法之人所运用的动机。需要注意的是,重生之人也不可能只运用在自然之国中由行为之客观道德性和上帝之预见产生的动机,他只会一直运用在神恩之国中由拯救之功和预见产生的动机,从而他因对基督的信仰而做善工。因此,基督教德性也远不同于哲学德性。即便二者的外在行动是一样的,并且都与神法(lege divina)相一致——当然不仅身体上的外在运动(motus in corpore externi)属于人类行为,而且心灵的内在活动(mentis actus interni)也属于人类行为;因此,如果你比较的是其心灵内在行为的原因、甚至心灵的整个内在状态的原因的话,那么两种外在相同的行为也可能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有人以平和中立之心思考我到目前为止所清楚表明的内容,那么他就会发现神学家关于神恩和善工的学说与我们的学说完全不矛盾;而且他还会发现二者是相一致的,从而我在上面(注释43)所指出的就十分明了了。当然下面还会再详细讲到。关于我在哲学德性和基督教德性之间所做的区别,也可查阅《伦理学》,在那里该区别是从诸基本伦理原则推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