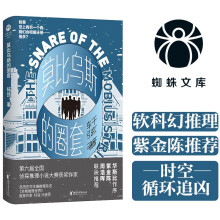魏晋玄学与儒道会通(节选)
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道家明自然,儒家贵名教,因而如何处理儒道之间的矛盾使之达于会通也就成为玄学清谈的热门话题。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的感
受全身心地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一种冷静的思考,毋宁说是对合理的社会存在的一种热情的追求。在那个悲苦的时代,玄学家站在由历史积淀而成的文化价值理想的高度来审视现实,企图克服自由与必然、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背离,把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转化为一个自然与名教、儒与道能否结合的玄学问
题,无论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蕴涵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表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就理论的层次而言,玄学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根据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对儒道之所同作了肯定的论证,这是正题。魏晋禅代之际,嵇康、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崇道而反儒;西晋初年,裴为了纠正虚无放诞之风以维护名教,崇儒而反道,于是儒道形成了对立,这是反题。到了元康年
间,郭象论证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把儒道说成是一种圆融无滞、体用相即的关系,在更高的程度上回到玄学的起点,成为合题。从思辨的角度来看,合题当然要高于反题,也
高于正题,在郭象的玄学中,关于儒道会通的问题似乎已经得到真正的解决。但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理论的逻辑并不等于现实的逻辑。就在郭象刚刚建成了他的体系之时,紧接着的八王之乱、石勒之乱立刻把他的体系撕得粉碎,从而使名教与自然重新陷入对立。我们今天回顾玄学的这一段历史,不能不带着极大的疑虑和困惑,追问一下儒道究竟能否在现实生活的层次达于会通?如果事实上难以解决,那么最大的阻力来自何方?既然困难重重,解决的可能性十分渺小,何以玄学家仍然苦心孤诣地在理论的层次长期坚持探索?他们的探索有没有给后人留下值得借鉴的普遍性的哲学意义?
其实,如果仅仅停留于理论的层次,儒道会通也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以迄于现代,没有哪一个哲学家能够对此作出逻辑上无矛盾的令人满意的回答,每作出一个肯定必然会被否定,每作出一个否定也必然会被肯定。正始玄学为竹林玄学所否定,竹林玄学又为元康玄学所否定,就是这种尴尬局面的历史证明。比较起来,还是那个无意于建立体系的三四流的玄学家的回答差强人意,是避免这种尴尬局面的最好的出路。《晋书·阮瞻传》:“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将无者,然而未遽然之辞,理智上不敢遽然言其同,情感上不愿遽然言其异,意思是莫非是相同吧,以一种反问的语气与人商榷,把难题的解答推给对方,而自己则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依违于同异二者之间,不作独断论的判定。即使自己摆脱了逻辑困境的纠缠,也给人们进一步的探索留下了广阔的回旋余地。王戎对“将无同”这三个字表示极大的赞赏,说明他根据自己的探索经验,深知此问题的难度,在开放复杂的心态上与阮瞻产生了共鸣。
儒道会通之所以成为一个难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所讨论的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而又永远不能解决的天人关系问题。自然即天道,是外在于人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必然之理,名教即人道,是内在于人的受人的意志所支配的应然之理。自其异者而观之,天与人分而为二,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天地不仁”,对人的价值漠不关心,始终是遵循着自己的必然之理独立地运行,而人则是创造了一套价值观念逆天而行,按照自然秩序所无的应然之理来谋划自己的未来。但是,自其同者而观之,天与人又合二而一,这是因为,人作为宇宙间之一物,首先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社会的存在,所以人既有自然本性,又有社会本性,既受必然之理的支配,又受应然之理的支配,这二者密不可分,结为一体,内在地统一于人性的本质之中。由此看来,如何处理天人之间的同异分合的关系就成了一个无法找到确解的难题,因为言其异者有同在,言其同者有异在,言其分者有合在,言其合者有分在,无论作出一种什么回答,都有另一种相反的回答与之形成对立。人们固然可以像阮瞻那样,为了保持某种心灵的宁静,不受难题的困扰,用“将无同”三个字作为遁词来回答,但是,机智的逃避产生不了高层次的哲学。哲学的本质在于面对无可确解的宇宙人生的难题进行穷根究底的追问而强为之解,即令最终免不了陷入矛盾片面也在所不惜。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基本问题而展开,由各种各样矛盾片面的看法及其相互之间的争论而构成的。
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对此问题提出了自成体系的看法而各有所偏,道家偏于天道而明自然,儒家偏于人道而贵名教,从而形成了对立的两极,并且由此对立而引起了相互之间的激烈争论。儒家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道家批评儒家蔽于人而不知天。事实上,道家言天未尝不及于人,儒家言人往往上溯于天,他们的思想体系始终没有脱离天人关系这根主轴,从两家运思的方向及其所欲达到的目标来看,都是着眼于天人之合的。但是,由于天人关系问题是一个善变的怪物,一当说它是合,立刻就分了,这就使得两家都免不了陷入某种矛盾片面,或偏于天道,或偏于人道。道家企图根据天道来规范人道,用无为而自然的必然之理来取代由人的价值观念所设定的应然之理,主张放弃人为的礼法名教的制作而返璞归真,恢复人的自然本性。照道家看来,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自然状态愈演愈烈的破坏,人的价值观念的丰富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社会的动乱,人际关系的冲突,都是由礼法名教之类的人为的制作所引起的,为了克服礼法名教的异化,消除动乱冲突的根源,只有把必然之理当作应然之理,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来重新设计一个适合于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儒家与道家相反,把人的价值观念置于首位,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不在于与禽兽相同的自然本性,而在于与禽兽相异的社会本性,如果不用礼法名教来制约自然本性而任其放纵无忌,恣意妄为,就会道德沦丧,人欲横行,从而造成社会的动乱,人际关系的冲突。因此,为了匡时救乱,儒家把应然之理当作必然之理,根据人道来塑造天道,主张则天而行,制礼作乐,确立一套文化理想和价值观念来发展人的社会本性,加强礼法名教的建设。儒道两家各执一端,自是而相非,究竟谁是谁非,是很难判定的。站在儒家的立场看道家,其缺点偏颇显而易见,因为道家过分地强调无为而自然的天道,否定了人的社会存在和文化积累。站在道家的立场看儒家,同样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因为儒家过分地强调人为的礼法名教,看不到礼法名教的异化会戕害人的自然本性,变成压迫人的工具。由于两家争论不休,互不相让,各自遵循自己独特的思路来展开自己的体系,这就在中国哲学史上开创了两个并行而对峙的思想传统,一个是道家的明自然的思想传统,一个是儒家的贵名教的思想传统,前者可称为自然主义,后者可称为人文主义。但是,就天人关系问题本身的内在逻辑而言,一当说它是分,立刻又合了。道家言天未尝不及于人,儒家言人往往上溯于天,都是受这种内在逻辑的支配,无法分割天人,而从事自然与名教的结合。道家所明之自然只有与儒家所贵之名教相结合,才能变成人化的自然,儒家所贵之名教只有与道家所明之自然相结合,才能克服异化现象,变成合乎自然的名教。这种情况迫使儒道必须各自向对方寻求互补,使之达于会通,一方面是并行对峙,另一方面又是互补会通,因而儒道两家的关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纠缠扭结,难以名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哲学思维正是由于儒道两家的这种复杂关系而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张力结构,始终是在同异分合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而蹒跚地前进。
西汉初年,黄老道家盛行,居于主流地位。黄老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以道家的自然主义为本,寻求各家主要是儒家与之互补,实际上是一个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相结合的体系。武帝之后,由于加强礼法名教建设的现实需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道家退居支流,儒家上升为主流。董仲舒曾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其所谓天,尽管经受了应然之理的主观塑造,仍为自然之天,即“阴阳之大顺”,本于道家的自然。由此看来,汉代儒家所致力建设的名教乃是一种合乎自然的名教,他们的思想体系也是以儒道会通为基本线索的。虽然如此,由于道家的思想包含了绝礼弃学、否定名教的一面,不适合当时的现实需要,所以汉代儒家在理论的层次强调儒道之异,以便更好地维护现实生活中的名教。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现实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名教被异化为一种无理性的暴力,道家在理论的层次对儒家所作的种种批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桓灵之世,一批昏君庸主、宦官外戚假名教之名行反名教之实。当时党人领袖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一些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聚集在李膺门下,“品核公卿,裁量执政”,企图凭借自由的文化舆论,以清议来维护名教。但是,掌握权力的执政者却以破坏名教为罪名对这一批真诚地维护名教的党人进行残酷的镇压,使之屈死狱中,或免官禁锢。这个延续二十余年震动极大的党锢之祸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究竟什么是名教?是统治者用以镇压异己的一种杀人的工具,还是规范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合理的秩序?如果是后者,那么其合理性的根据何在?有没有一个判定其为真名教抑或被异化了的假名教的客观标准?人们根据自己对现实困境的真切感受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终于在曹魏正始年间,提炼升华为一个儒与道是同是异、自然与名教是分是合的玄学问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