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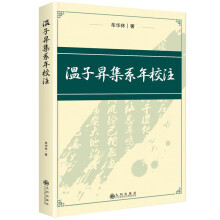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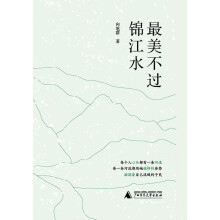
《幸福》是美国知名作家和表演者希瑟.哈芬(Heather Harpham)的回忆录,感人至深,书写了对于生命、家庭、爱情、亲情的感悟。当希瑟和布莱恩在纽约相遇时,希瑟是一名从北加州而来,怀抱着嬉皮梦的自由表演者和写作家;而布莱恩是一名相对严谨的老师和作家,崇尚着极简生活:每天穿着一样的服装、吃一样的晚餐。在强烈的两相对比之下,两人很快地被彼此极端的特性和共通拥有的才华所吸引,并坠入爱河。遗憾的是,确定关系之后的两人,无时不被迥异的价值观和生活模式所困扰着,毕竟爱情和婚姻是不同的。两人终究走到分岔路口的那天,喜爱小孩的希瑟热切地宣布她怀孕的消息,然而布莱恩却始终不想要孩子……两人决定分开,希瑟回到她的家乡加州马林区,在两条可爱的狗陪伴下,孤单地准备生育她的小宝贝。然而,两人都未曾想过故事会这样发展!他们的女儿格蕾西,在一出生就被宣布罹患了罕见且难以诊断的致命血液疾病!在责任心和爱的趋使之下,希瑟和布莱恩谨慎地再牵起彼此的手,希望能共同面对这个上天给出的难题。种种艰难很快席卷而来,医生宣告格蕾西的希望,将是来自手足的骨髓移植……
——《书单》
一个关于找回险些失去的爱的故事。
——《人物周刊》
在这部令人动容的回忆录中,哈芬描述了她在生下孩子之后的温暖、无所畏惧的诚实、悲伤背后的幽默……哈芬发自内心地写出了家庭的联系,以及为了抵达幸福而必经的崎岖旅程。
——《出版人周刊》
哈芬的作品是温柔的、坦诚的,《幸福》是一个关于生命和死亡、疾病和健康的故事,*重要的是,它是关于家庭的。
——《明尼亚波里星坛报》
这是令人心灵震撼的回忆录。哈芬重温了她真实的治愈之旅,在这个过程中,被挽救的不只是她的孩子,还有她的婚姻。
——奥普拉个人网站
《幸福》是希瑟·哈芬和她患病孩子生活的故事,既令人心碎、惊愕,又如此天才。
——《芝加哥论坛报》
带着智慧、情感、同情,哈芬告诉我们正是那些崎岖的道路*我们通向我们想去的地方。
——安·胡德,《红线》作者
《幸福》完美地呈现了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子关系和伴侣关系。
——苏珊·奇弗,《天黑前归家》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