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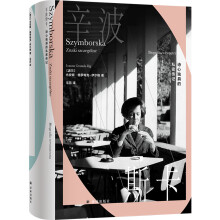
《安德烈·托尔斯泰》是关于托尔斯泰家庭的长篇小说,作者主人公安德烈·托尔斯泰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第九个孩子,作者通过描写安德烈从军、参战,到回乡、去世及在此期间一系列的心理历程,解开了主人公安德烈与父亲托尔斯泰及母亲索菲亚温情又有矛盾的关系,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托尔斯泰和他的家庭生活的独特视角。
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这片陌生大地上的天空与他童年时的亚斯纳亚一样,布满繁星,黑得令人害怕。
他感到心一直在激烈而又不规则地跳动,发现双手在颤抖:就在几分钟之前,就在火车重新启动和最后一声汽笛鸣叫之前,在一片黑压压的士兵斗篷中,在熙熙攘攘的躯体、苍白的面孔和闪亮的金属片之中,他似乎看到了父亲的身影,啊,就在人头攒动的车站出口处,他好像真的看到了父亲——尽管他心里明白,此时父亲在几百公里之外。真像从天而降,父亲一下子就站在那里,一只手紧紧抓住那个易碎的木围栏,另一只手拿着那顶浅灰色毡帽。尽管父亲所在的地方与他成功挤上的那列火车之间相距遥远,他似乎仍能清楚地看到那微微的驼背、深陷的面颊,斑白的两鬓清晰地被黑色的羊皮大衣反衬出来——他也看到,父亲那明亮、刚毅的目光对着他,带着他熟悉的父亲所有的深深的蔑视和慈爱的表情。有一瞬间,他觉得父亲挥动帽子向他致意,特别奇怪,那姿态似乎更多的是欢迎而不是告别。
他突然想起几周前那个同样漆黑、繁星密布的晚上,父亲把他送到图拉火车站。父亲那时应该处于怎样奇妙的精神状态下啊!——他现在震惊地想到。
父亲对他的决定是多么深恶痛绝!杀人,参加战争,还美其名曰保卫祖国——他不是经常听父亲这样说吗?——违背父亲的信念。啊,他的父亲甚至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向他表示,不幸当中的万幸是,他,安德烈,作为传令兵被打死的风险很大,而他自己射杀和打死别人的机会很少。
尽管最近一年父亲在信中反复强调,儿子对他是多么重要,他很爱他。
父亲在图拉火车站时不是兴高采烈吗?他记得父亲张着没牙的嘴对着他微笑,不止一次笑出了声。他甚至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这亲昵的动作几乎令他,安德烈,大声哭起来。
“当然,”他继续想,“父亲仅仅把我送到图拉。没有再远送,没有最终送到我的军团驻扎地坦波夫,那里是我最终开拔上前线的地方。”
不过,难道我希望这样吗?
此时火车已经接近奔萨。明天,最迟后天,他们就将穿过萨马拉(古比雪夫)西部辽阔的草原,随后就是那座城市,最后到达东边二十公里处曾经属于他自己的同样辽阔的土地,童年的时候他在那些地产上度过很多夏天,猎兔、骑马、住帐篷,喝热乎乎的马奶,吃有新鲜水果的野餐,不过他对那片贫瘠的土地一直没有好感,恰好在四年前他违背父愿卖掉了。经过萨马拉、乌法、兹拉托乌斯特和库尔干——三周以后,甚至更长一些时候,他们就将到达满洲里,逐渐靠近辽阳前线。他的眼睛疲倦地眨着,感到很难受。车厢里闷热,充满烟和汗腥、困顿和廉价白兰地的臭味儿,在此之前他曾经体验过这种令人恶心的感觉。此时这一切又以某种自然的、完全不可思议的形式凑在一起了:难以忍受的拥挤、苍白和长时间未刮过的脸、火车窗外的黑暗、害怕又庆幸的复杂心情和想到最终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轻松感。他不是第一次有这种特别和无奈的感觉,当他把手伸进军服口袋时,发现里边有一个带木樨草半碎花瓣的信封和妻子的一封信——一封没有责备而是充满温情的信,让他心里很难过,——盖上刻有主人姓名首字母的金质鼻烟壶,还有一把热乎乎、有点儿发黏的枣,这是母亲在他学会吐核后就开始安慰他用的。
他周围的人似乎都睡着了。一种深沉、奇特安静的睡眠。只有紧靠窗子的那位传令兵没有睡。黑暗中传令兵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向前看着。他尽量不让自己朝这个人的方向看。但是每一次他们的目光还是在窗玻璃上快速悄然交会时,他觉得对方的眼睛里仿佛有一种审视的目光,一种好奇,让他感到害怕又迷惑。
这个陌生人想对他怎么样?
他突然感到他仇恨他,还有厌恶。啊,他实在是讨厌这个陌生人!这个荒唐的有点肥胖的下级军官有着打过蜡的胡须、大鼻子和圆鼓鼓的肚子。不仅是这个下级军官,他还讨厌其他所有的人。所有这些陌生人似乎都能从他的脸上读懂他竭力掩盖的东西——他们明显能看出他是将被打死的人之一。他将是暴尸战场上的人之一,他的尸体将在炽热的阳光下变黑,腐朽,慢慢分解。
这就是他此行唯一可能的目标。
啊,这确实是他唯一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