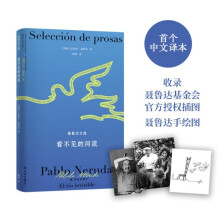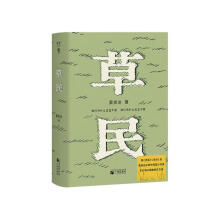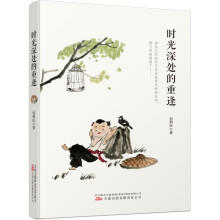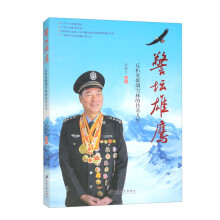笑吧,笑翠鸟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去过2次澳大利亚了,但按照我爸爸的说法,我还不能算是真正去过。他是在我表妹乔安家发表这一高论的,那年圣诞节前我们两个正好去她家作客,在这之前还有一句同样咄咄逼人的话。“其实,”他说,“戴维读书的本事比他写书的强多了。”这句评语来自一个自从1996年的《戴夫?斯托克顿的推杆致胜》就再没看过书的人。他也从没去过澳大利亚。连那附近的国家都没去过。
“那不要紧,”他告诉我,“想真相见识一个国家,一定要到乡村去,你只能说自己去过悉尼。”
“还有墨尔本和布里斯班,”我说,“乡村我也去过。”
“别瞎扯了。”
“好吧,”我说,“给休打电话。他会给我作证的,还可以发照片给你呢。”
乔安和她的家人住在纽约州的宾厄姆顿。它们不常能见到我爸爸和我,所以我们两个不像这样坐在人家的桌子旁边斗嘴就太不应该了,活像一对老夫妻。由于感到尴尬,我放弃了乡村的话题,而我爸爸也转头去谈论其他人的缺点了。我的思绪回到了去年夏天,回到了从伦敦飞往悉尼的长途旅行。当时我去澳大利亚出差,由于机票有人买单,返程时还可以经停日本,休便和我一起来了。并不是说澳大利亚有什么不好,而是我们已经去过一次了。而且,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飞行,走下飞机舷梯时理应进入一片新天地——比如说,水星,或者最起码也得是墨西哥城吧。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澳大利亚看上去是那么熟悉:同样宽阔的街道,同样高耸的写字楼。基本就是穿着丁字裤的加拿大,或者说,最初的印象是这样的。
虽不愿承认,但我爸爸对于乡村的看法是对的。休和我并没有见识过太多的乡村景色,要不是那个在墨尔本出生并成长的女人帕特,休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开开眼界。我们早年在巴黎与她相识,那时是七月中旬,她到那里度假。在我们的起居室里酒过三巡后,帕特的脸上挂满了汗水,她教会我们“喊”(“shout”)的一种特殊用法;“我喊午饭”(“I’mshoutinglunch。”)表示午饭由你请客,而且你不希望有人和你争。“你还可以说,‘这由我喊’,或者,‘下一杯我喊’。”她告诉我们。
那次见面后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等到我的工作结束,并得到了一天半的自由活动时间时,帕特自告奋勇当我们的向导。第一天下午,她带我们在墨尔本转了转,还喊了咖啡。第二天早上,她来宾馆接我们,然后开车带我们去她口中的“野外”。我还以为是一片遍布沙子和人骨的荒原,结果发现完全不一样。澳大利亚人口中的“野外”就是森林。一大片森林。
但首先我们要离开墨尔本,再穿越貌似无边无垠的市郊。当时是八月,正值严冬,我们把车窗都摇了起来。途经的房屋都是木制的,很多还在后院四周竖起了高高的栅栏。这些房屋与美国的有些许差别,但我又说不清楚区别在哪儿。“是屋顶吗?”我心里想,“还是墙板?”帕特负责开车,在驶过一个通向购物中心的岔路口后,她让我们在心中想象一台4个灶眼的炉子。
“烧煤气的还是用电的?”休问,她回答说无所谓。
那不是一台真正的炉子,只是一种象征,用来说明她在一次管理人员研讨会上听来的观点。“一个灶眼代表你的家庭,一个代表你的朋友,还有一个代表你的健康,最后一个代表你的事业。”她继续解释说,为了取得成功,你必须主动关闭某个灶眼。如果想非常成功,就要关闭两个。
帕特有自己的公司,效益不错,所以才能在55岁退休。她有3处房产和2辆汽车,但即便没有这些东西,她看上去仍然是一位发自内心快乐的人。单凭这一点就算得上成功了。
我问起她关闭的是哪两个灶眼,她说首先是家庭,之后是健康。“那么你呢?”
我想了一会儿,说关闭了朋友那个灶眼。“这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但自从遇见休之后,我就不再勉强自己了。”
“还有别的吗?”她接着问道。
“我想,是健康吧。”
休的答案则是工作。
“还有呢?”
“只有工作。”他回答说。
我问帕特她为什么会切断与家人的联系,她回答时没有丝毫苦涩,告诉我她的父母都是酒鬼。他们喝丢了工作和信用记录,又因为破产不得不到处漂泊,搬家往往都发生在半夜。这样的生活使得养宠物成了一种奢望,即便是短暂饲养也很难,但帕特和姐姐还是养了一只羊。那只公羊又老又脏,她们叫它“普雷斯顿先生”。“他很可爱,性格也好,直到有一天我爸爸带它去剪毛。”帕特告诉我们,“它回来时身上秃了好几块,还有一些可怕的伤口,像是被刀扎的。然后我们搬进了公寓,只好把它处理掉了。”她盯着自己紧握方向盘的双手,说:“可怜的普雷斯顿先生。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起它了。”
这时我们终于抵达了“野外”。休指着窗外一团脏兮兮的皮毛,就在一棵倒了的树旁边,帕特一下子激动起来,大喊着“路毙!”。随后她停下车,想走近去看看。自从离开墨尔本,我们便深入了丘陵地带。气温相当低,地上有不少灰色的雪堆。我穿着毛衣和外套,还是感觉冷,在走向尸体的路上一直在发抖,直到看见那是……什么东西?“小袋鼠吗?”
“沙袋鼠。”帕特纠正了我的说法。
可怜的小家伙被撞了,但并未遭到碾压。身体没有腐烂,也没有破损,那身不怎么样的皮毛倒是令我吃了一惊。好像是兔子和驴子杂交而成的。还有那条尾巴,让我想起了长矛。
“休,”我喊道,“过来看看沙袋鼠。”
休相信,在路边兴高采烈地观察动物尸体的人,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杀死这些小动物的凶手——并非偶然,而是蓄意为之,开车碾过时还在哈哈大笑。因此他坚持留在车里。
“你会后悔的。”我还在劝他,边说边从嘴里喷出一股热气。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