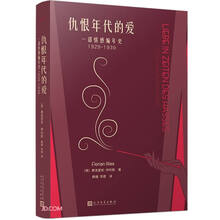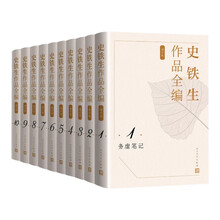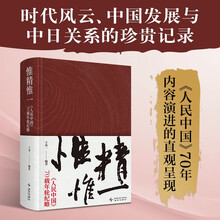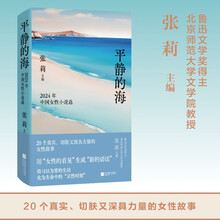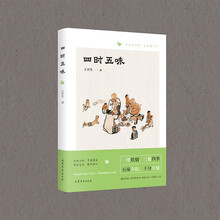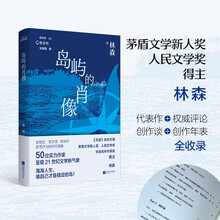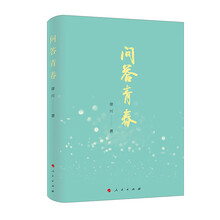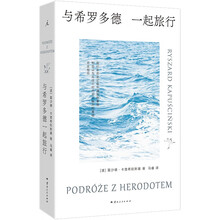走近晚年的陈独秀①
11日下午,我怀着一份复杂的感情来到渝郊江津市拜谒“陈独秀旧居”。车子盘桓在崎岖的山路上,我的心在汹涌地澎湃着陈独秀跌宕起伏、曲折伟奇的往事。
我和陈全、阙洪玉等友人在江津市鹤山坪一座旧式的四合院门前驻足。
鹤山坪是方圆几十里的丘陵地带,是个山区。石墙院属于清朝进士杨鲁承的宅院,四合院,过去有石头砌成的两道外围墙,现在没了。坐南朝北对着长江的是正房。主建筑正堂七间,瓦房早已陈旧。当年陈独秀和第三任夫人潘兰珍就在一间正房里寝居。
陈独秀自幼丧父,6岁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7岁过继给四叔陈衍庶为嗣子。20岁丧母。嗣母就是一生未育的四婶谢氏。1939年,78岁时的嗣母在潦倒、失意、穷困、凄愁、蒙辱的陈独秀身边客死他乡。陈独秀曾哀伤地对三子松年说:“等战争结束,我们回安庆时,一定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要让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做孤魂野鬼,你爹心里是不会安宁的。”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两女,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不识字。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执意不从,两人争吵以至于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进步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在高君曼病故后,潘兰珍在上海与陈独秀结识,开始照顾年长自己3l岁的陈独秀。潘兰珍与陈独秀虽不是结发之妻,但却是患难之交。陈独秀南京坐监,她就无微不至地照顾陈独秀,共同生活10年。人世间,于落难不弃,对富贵不附,实为做人的美德。
往东两间厢房,为陈独秀的会客室及其里面套间书房。陈独秀的灶房也在东边。陈独秀居室是东数第二间正房。陈独秀为已逝杨鲁承整理遗稿,杨家对陈独秀颇为敬重,住房也不要钱。我们参观了陈独秀潘兰珍居室、书房。陈独秀用过的桌、椅、床、被,潘兰珍的花衣服,还有他们二人弥足珍贵的照片。
房外是陈独秀用过的水井。走出后门是竹林,是陈独秀经常散步的地方,透过竹林,可以看到长江。极目远眺,重峦叠嶂,青山连绵。
陈独秀在江津之初心情非常沮丧难挨。寄人篱下的陈独秀感到说话、做事都得看房东邓太太的脸色极为苦恼,更有那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污言秽语不时冲进半聋不聋的耳鼓里。陈独秀和潘兰珍忍气吞声,但邓太太终燃、“战火”,双方唇枪舌剑。忍耐度日的陈独秀愤然择房另居。这就是眼前的这座鹤山坪石墙院。它述说着一段让你遐思冥想、悠远而感伤的故事。
陈独秀誉其有“世外桃源”之感。说:“幽静安谧,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是潜心著述的好地方,正满足了我隐居的心愿,难觅的栖身之地啊!”后来,陈独秀带领杨家佣人将院内外扫除一新,栽上花、植下树,又辟菜园种上瓜果葱蒜,著述之余,领略劳动果实的甘美。
据说,陈果夫、陈立夫宴请出狱后的陈独秀,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直白:“……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陈独秀选择了隐居式的颠沛流离生活。他于1938年8月3日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来到了江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和戴笠经蒋介石允许后,曾提着水果、茅台酒等礼品微服拜访陈独秀。开始,陈独秀拒不接见。后来,两人找到陈独秀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通融,才得以见面。陈独秀表示,自己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但不问政治,也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独秀请胡宗南和戴笠转告蒋介石,要好自为之。蒋介石得知陈独秀的答复后说:他还是识大局的。
在陈独秀晚年的岁月里,陈独秀有一个忘年交,叫杨朋升,他使我感念数日。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朋升信函达40件之多。其间,杨3次接济陈共计2300元,转交他人赠款亦3次计2200元,且赠信封及用笺,使陈独秀维持生计之外,得以著书立说。四面楚歌的陈独秀和杨朋升的交往使我感念数日。
杨朋升是四川渠县人,小陈独秀21岁。他青年时就读北大,喜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文章。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荐,杨朋升师从北大文科系主任陈独秀,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可谓名副其实的忘年之交。杨朋升两度留学日本,归国后入军界。平生好书法。“一·二八”淞沪战役时,任88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9月,陈独秀到达武汉,杨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任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朋升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1938年,武汉沦陷后,两人又一前一后来到四川,杨朋升因对国民党不满,寓居成都修建“劲草园”,沉溺于书画。而陈独秀也内迁至江津。从你来他往诸多信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虽曾为师且年龄较长,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均称杨为“老兄”,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均为“弟独秀”,书信最长的有3页,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
在信中,两人或作学术探讨,或倾诉衷肠,其中一封复函杨朋升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感念蔡元培对自己入狱后的多次声援营救。还有其中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陈独秀的嗣母于此前两个月去世,其悲伤之情在给杨朋升的信中表露尽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1942年4月,杨朋升收到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陈独秀对杨朋升多年的资助“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陈独秀病逝后,杨朋升很悲痛,在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5月27日逝世于江津,4月5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