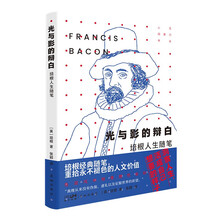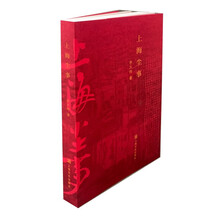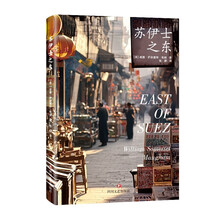命若琴弦乡村二胡手王麻石死去的那年我正好十二岁。当我伫立在2006年的时间坐标上。回首眺望。看见我的少年和青年如娇嫩的花瓣纷纷坠落,它们在黄尘与风雨中褪尽颜色,零落成泥,灰飞烟灭。
怀旧之水如此清冽,倒映着色泽陈旧的乡村背景。记忆斑驳、杂乱,许许多多的事情没有结局,它们如烟一样袅袅上升,淡人渺远的暮天。
当再次写下“命若琴弦”四个字,我的眼前似乎展开了一条奇妙的时光隧道,我一次次地往返其间,期待在某个瞬间,发现一些线条,它们或模糊或清晰,却暗指着命运的走向,顺着它,我能进人事件的内核。
是的,正如你猜想的,我不是第一次写他或她。事实这是第三次。我第一次动笔是在十年前,那次我虚构了一个残酷而绝望的结尾。王麻石在一个灼热而焦躁的中午.扼住了哭闹不休的婴儿的咽喉,他心中的魔狰狞着,在杀死了孩子、杀死了希望之后,又杀死了自己。
第二个版本静静地躺在我的电脑里.我曾经把它贴在一个小说论坛。我看着它如一枚滑进湖水的卵石,悄无声息地沉入水底。那个骇人的尾巴已被我一刀割下,我试图在悲苦的旋律里凸现一缕温情,像天边的早霞,挣脱黑暗的羁缚,温暖婆婆与儿媳盛大的苍凉。在那两个虚构的版本里。这是永远朝着一个方向的两个女人,她们合力摧毁了一道道防线,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制造了一出悲剧。
所有的悲剧,归根结底,都是人性的悲剧。邪恶源自人心,冷酷源自人心,疯狂源自人心。而我要说的却并不是邪恶、冷酷与疯狂,它或许只是无奈。
我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闪烁其辞,而不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呢?长久以来,这个乡村故事一直纠缠着我,它们像一根根荆藜,扎在我的身体里。
我曾经把它说给我的一个朋友听。在那个陌生的城市,我的语言絮叨.冗长,如纷乱的落叶,它们没有方向,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在迷宫般的黑暗里,如一只懵懂的蛾子寻找着死亡的人El与虚无的光明。我坚持着把它讲完,我感觉到他隐忍的焦躁,他的脸在诡异而夸张的霓虹里渐渐失真。那一层微笑却一直都在,他微笑着说:“这有什么意义呢?你想表达什么?”我愣住了,愣在微笑里。我感觉自己身体里的热浪正迅速退却,它们潮湿而冰冷。
是啊,这有什么意义呢?而且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首先,这样的故事毫无新意,你给它一个乡村背景或者给它一个城市背景,有什么区别呢?我在他的微笑面前沉默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话语一定要穿上意义的盔甲,一件事情的发生与结局和一朵飘忽的云彩,它们的意义是否一样?有的时候,看见与说出也许就是意义本身。
回到故事。
回到故事的时候,我也回到了童年。我在那样的年龄势必不能完全读懂隐藏在事情后面的真相,那么我就撇开真相,只端出自己知道的,好吗?王麻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二胡。听过他琴声的人都知道,他的二胡拉得好。在那个京剧盛行的年代,公社宣传队里没有京胡手,王麻石凭借一把二胡,竟也可以扯出激越、高昂,将一台戏衬托得丰满而热闹。他的琴子一响,可以扯得人笑,也可以扯得人哭,这样的本事自然吸引了一些姑娘~ItllII~,金花就是因为爱听他的琴声,自己走进了他的家门。但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王麻石已经轻易不操琴了,他总是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这是一句电影台词,经了王麻石的口,好像真添了无限的沧桑。王麻石那时也就三十出头,但他已经认为自己老了,看上去.他也确实老了。青灰灰的一张瘦脸,颊部深深地陷落,眼白不是白色的,而是黄晶晶的,和他早逝的父亲一般模样。三十岁的王麻石娶了金花多年,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金花人高马大,脸上红桃花色的。不能养孩子可是件大事,一个不能养孩子的女人通常是会遭到婆家的唾弃的。婆婆是个明白人,她知道问题多半出在自己儿子的身上,而她不能坐视不管。
婆媳俩一个推波助澜,一个半推半就。一切就这样开始了。王麻石被母亲与妻子推到一个尴尬而屈辱的境地。
这不是简单的偷情——性一经上升到生育的高度,上升到家族的传承,付出就是整个家庭的付出,牺牲也是整个家庭的牺牲。
当金花的肚子山包一样隆起的时候,王麻石像枯枝渐渐失去了最后一抹青痕。现在想来,王麻石得的应该是肝病,他经年喝着黑色的汤药,那些液体渗透到他的身体里,像一株植物经过长期的浇灌,散发着苦涩的气息。他面对金花变化着的身体,长时间沉默,没有喜,没有恨,好像那是一件与他完全无关的事,至于他的内心,煎熬也罢,平静也罢,那似乎已经不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了。但他终于没能等到那个生命的降临。
这当然并不是结束。真正的结局像一块黑色的礁石,搁浅在许多人的记忆之河,无法轻易绕过。
婆媳反目成仇,为了孩子,对簿公堂。一边是年轻的母亲,一边是年迈的祖母,谁更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法律公正、冷漠,对艰难生长着的枝蔓视而不见,它直视着挺拔的枝干,认为这就是结果。不错,这正是该有的结果。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婆婆的泪。她是王麻石的母亲,她是金花的婆婆,她还是孩子的祖母。现在她什么都不是了,她什么都没有了。不仅是她,所有人都认为金花绝情寡义,不明白金花为何要夺走这个孩子.她还那么年轻,以后可以再生再养。但金花这时好像鬼附了体,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金花带着三岁的孩子借助法律成功地逃离。
那块礁石浮出了水面,它冰冷、坚硬,冒着森森的寒气,多少年来.我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成功地表达,或许正缘于此。它既简单又复杂.可以用“人性”二字来概括。
王麻石的母亲淹没在绝望的死海,她拉住一只只熟识或不熟识的手,就如抓着了救命稻草,在一声“我的命好苦呀”的长叹后.开始周而复始的哭诉。她的眼泪和诉说,在黄昏的路口与河滩,在初春的青草与冬日的严霜中,潇潇而下。她稀薄的白发如乱草般没有方向,只有风的方向,只有时间的方向。那渐渐遥远、黯淡的声音,苍老而无助。
金花的决绝也许正是缘于内心的软弱与恐惧。她害怕面对那双幽怨的眼睛,她不敢看那把落满尘土的二胡,它有时突兀地响起来,在黑夜深处,绵绵不绝,她怎么敢把孩子留在这里呢?怎么敢?要把这些破碎的夜晚和不堪回首的往昔从记忆中抹去,她只能选择走,必须走。
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纤弱的生命的叹息,在时间的旷野漫散,如隐隐的琴音,飘忽、不可紧握和把持。在静谧的空间里,我听见时间的指针轻轻颤动了一下,而那块礁石已经不是黑色的,它复杂模糊,有着太多我不能破释的谜和说不透的理。但我终于把这个故事说了出来,或许我落入了俗套的陷阱,正以一种自由落体的姿势跌落,但我说出来了。无论如何,这才是最重要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