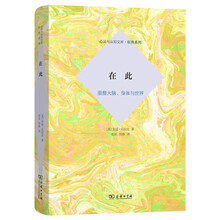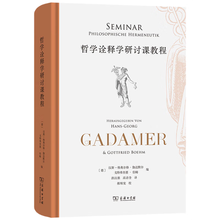围观两位哲学家吵架是怎样一种体验?
如果冲突双方碰巧还是宗师级的人物,学术造诣之外还拥有迷人的个人魅力呢?
本书讲述的正是两位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之间的一次冲突。1946年10月25日,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个挤满人的房间,发生了他们二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而这次会面并不愉快,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产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剑拔弩张、兵刃(火钳)相见。这一插曲成为了哲学史上的一段传奇,几十年以来人们一直津津乐道。本书从维特根斯坦与波普尔的这次争斗展开,梳理了20世纪的哲学史,是哲学、历史和传记的交织。透过BBC制作人的生花妙笔,你不仅可以走近维也纳世纪之交的动荡和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悲剧,更可以一窥罗素等战后活跃在剑桥讲台上的那群哲学怪咖的生活。
读罢此书,你或许会为这本书的文学性感到惊讶,符号化的哲学人物活了起来。哲学史不会记述或者主动错过的,恰恰是哲学家身上有温度、有人味儿的一面。而这些,你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