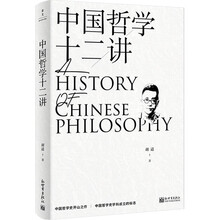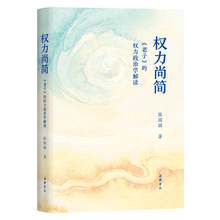第二章儒学、中国性以及“仁”的道德人格
鉴于溺杀女婴、收养童仆或童养媳、纳妾、缠足和守寡等臭名昭著的社会行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性别歧视在前近代中国甚为普遍。这些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或地域扩展到更大的范围。由于儒学在自我历史叙述中被诠释为一种有关自我修养、关爱和恰当关系的学说,因而这些行为不但反映出不平等的性别地位和权力,而且对国家所推崇的儒家道德教化产生了质疑。然而,尽管儒家道德作为国家所推崇的正统思想,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残酷压迫却一直存在于前近代中国。简单而言,在帝制中国,儒家道德教化和性别压迫的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隙。性别压迫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而儒学作为一种理念体系助长了社会对女性的虐待。女性通过何种方式才能在有关道德伦理和礼仪得体的儒家著述中被视为积极的参与者?
儒学与中国性别歧视主义之间的相互关联是复杂的。我们首先应该抵抗将儒学和性别压迫二者视为具有密切关系或显著关联的诱惑。为了提出具有批判性的假设,致力于中国性别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需要即刻面对如下问题:“什么是儒学?”以及“采用何种方法能够支配例如缠足、纳妾、对守寡的狂热等被归因为儒家学说的社会行为”?换言之,我们如何识别缠足、纳妾等行为中的“儒家性”?与此相反,我们如何识别作为整体的儒学中所包含的“性别歧视”成分?最后,在“儒学”和“性别歧视”之间是否存在着这种必然的因果联系?简言之,“儒学”中的性别歧视主义彻底吗?为了找寻上述问题的答案,在理解儒学作为一种理念体系、它在华夏文明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它被历代王朝所利用和滥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怀有诚恳的态度。否则,任何将压迫女性归因于儒学的论断都会显得肤浅。
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女性研究的高潮以来,甚至远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女性的早期西方论著通常将儒学描述为一种男权至上主义和父权意识形态,并且将其视之为中国女性压迫问题的根源所在。较为显著的例证是1974年法国早期女权主义作家茱莉娅·克丽斯蒂娃(JuliaKristeva)在有关中国女性的著述中冒失地将一个章节定名为《孔子——女性的吞噬者》。①直到1995年左右,学者们仍然将儒学以及儒学的大部分特质视为一种父权意识形态,并且认为这种与现代社会或所谓的优越者——西方生活方式毫不相干的父权意识形态应该被彻底抛弃。正如卢蕙馨(MargeryWolf)对杜维明有关新儒学之通俗诠释的评论那样,“儒家准则定义下的层级权威系统的合理构造以及父权制家族体系的秩序井然似乎与这样一个跨国公司设在富士园,而来自上海的年轻人正瞄准斯坦福工商管理学硕士的时代不相适宜。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儒家的经典仍然畅销,而一位哈佛的杰出学者——杜维明对于新儒学的重新诠释和现代社会的生存指南竟如此接近”②。卢蕙馨在评论中对儒学的冷嘲热讽由此可见。按照她的观点,儒学这一古代中国毫无益处的思想观念几乎等同于父权制和厌女症(misogyny)。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