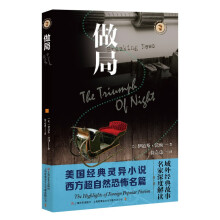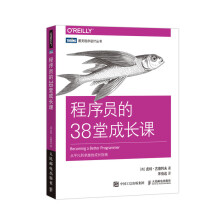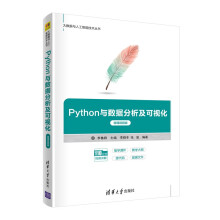媒体书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
有人这么评价黄仁宇的这部书:以短短的20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他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显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般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证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黄仁宇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假设多于实践”,“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一部二十四史,绝不是二十四姓的家谱。将一个朝代的盛衰,绕开道德评价的怪圈,而转作对一个组织结构的效率和能力的考察,黄仁宇为解读历史提供了相当精彩的角度。
古代历史上,游牧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原农耕国家的心腹大患,并往往能取而代之,原因不是野蛮战胜文明这类不痛不痒的空话,而在于游牧民族结构简单,行政效率高,在有限的资源分配和作战调动方面要比大帝国显得更有活力。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制度危机。由周公开始,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总是力图通过人为的尽善尽美的组织方案来治理这个大帝国,但庞大又不按专业技能分科的官僚组织,仅靠教化和纪律来控制,是注定不可能适应新时代的。
翻读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笔者最大的感触在于传统社会(包括意’识形态)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作者一再强调中国传统社会不能用数字来管理,指的是旧中国一直缺乏量化管理的思维。道德判断代替价值判断现象越盛,则实际的技术手段就越受局限。
黄仁宇认为,在中国早期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域广大,在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从西周开始,就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即他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这种设计在秦汉以后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社会,其立足基础是遍布全国的均匀的农村组织,上端是同样结构均匀的有纪律的官僚组织,这样使中国的朝代以一种权力的架构放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基础之上,难以在短时期内用和平方式改造,它在明清时期丧失了其扩展性和开发性,走向内敛和非竞争性,也是中国在近代走向落后和遭受屈辱的历史根源。从秦汉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始终处于中央集权的官僚统治之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不待社会多元化就先已构成集权体制,汉代采取不断加强中央统治的政策,通过将宇宙观、天候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哲学将专制皇权合理化,构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促使中国政治体系早熟,并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到清代,这一系统使中国保持了长期的秩序与稳定,但是也使国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因为它组织简单,效率低下,是既缺乏弹性又欠实力的政体,结构上的脆弱使其对外界的压力缺乏抵御的实力,难以成为可资改造利用以增进民权或者转变为多元社会的桥梁。
在经济上,以小自耕农为主,所以它一直是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使得国家的财政资源过于分离散漫,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原则,造成经济上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并且中国经济以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并以之为全国的标准,是牺牲质量以争取数量,无意于国民经济多元化和商业的充分发展。作为政府本身对服务性质的组织与事业不感兴趣,更没有司法和立法的组织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和现实。由于缺乏节省人力的动机,农具在长时期内没有显著增进,仍然广泛使用。农村经济既缺乏地区间的联系,又没有各行业间的经营。政府筹措的办法,或是直接科敛,或是向下层加大压力,勒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报酬的工役。村民之间的遗传、婚姻、财产交割、殴斗纠纷等多由家族内部解决,虽然减轻了衙门的任务,却长期阻碍了民法的展开。北宋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作为行政工具管理国事,但是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新法未能成功施行。到了明朝,洪武型财政过于迁就农村经济的习惯,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背世界潮流而行,它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的商业作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政府的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财政的实施缺乏强制性的管制工具,它的账目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造成技术上的困难,在执行上愈到下端就愈加松懈,结果行政效率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年久失修,贪污行为无从抑制,灾荒不能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匪为盗,使一个朝代走向灭亡。
在政治上,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就造成一种专制体制,可谓在政治上早熟,它缺少相互制衡机制,它的基础是儒教的纪律,这种政治权威的负面性格十分明显,当这纪律被破坏时,此极权也无法维持。事实上,维持高度的中央集权仅有纪律是不够的,国家的大部分成就,实因恐怖政治而获得,从长远角度看,也阻碍了法制的成长。因为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其影响所及使得官者与举者之间保持恩泽关系,而将公事视为次要,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尊重法治,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易于造成整个政体的瓦解。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样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由于帝国官僚机构的执行全靠官僚的名誉自重,容易造成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使舞弊、贪污腐化和欺诈的现象相当普遍。“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段,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由于官僚主义依靠社会价值作为行政的工具,因此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现在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组织上的重荷与结构上的大而不当是其根本原因,不能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