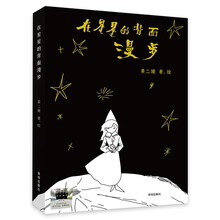相遇之初的惺惺相惜 20世纪20年代初,林语堂留学归国,被胡适引荐到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这个时候的北大,可以说是群英聚会,同时也是学术辩论气氛最热烈的时候。引荐林语堂的胡适此时已经与鲁迅发生了分歧。林语堂虽然和胡适交往深厚,却出人意料地加入鲁迅领导的“语丝社”。
在1925年的学生游行中,林语堂和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在和军警冲突中,林语堂被砖头砸伤额头,留下了永久的疤痕。他的激进行为得到了鲁迅的赞赏,此后,鲁迅两次致信林语堂,此时的林语堂热血激昂,鲁迅的赞赏令他非常激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当时刚刚担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写下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与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互相呼应,表明立场,支持学生运动。1926年邵飘萍遇害后,很多文人和学者南下避难,林语堂也到了厦门大学任教。不久,鲁迅也离开了南京,接受林语堂的邀请,前往厦大。
厦门大学的生活,并不十分愉快。鲁迅和林语堂屡屡遭到排挤,在这样的困境中,两人的友情却愈加深厚起来。鲁迅曾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道— — 其所以熬着者,为己只是有一个经济问题,为人就怕我一走,玉堂(即林语堂)立刻要被攻击,因此有些彷徨。
此语足以看出两人当时的友情十分深厚。
就在学生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语丝》的成绩也越来越辉煌。但是,鲁迅和林语堂的友谊却出现了裂痕。在武汉的六个月,使林语堂渐渐感到对革命的厌倦。他觉得革命是“吃人的斯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林语堂选择退出,并决定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在自己的文中写道——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不久之后,林语堂和另外几个人办起了《论语》,他喜欢用幽默的笔触调侃生活中的各种小事,这让鲁迅不能理解,他觉得在如火如荼的战斗中,根本没有幽默可言。虽然在思想上出现分歧,但是在私下里两人还是会经常碰面。
这期间,林语堂在《论语》上发表了—篇《我的戒烟》,鲁迅公开批评他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鲁迅说:“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分歧之后,罅隙暗生 后来两人因为政治事件避居上海,都以写文为生的时候,分歧进一步加大。那期间,鲁迅将文字变为“匕首”、“刺刀”,继续不屈不挠的斗争,林语堂则用幽默、小品的文字,曲折地表现自己的不满。
1928年8月底,在一次私人聚会之后,发生了文学史上称为“南云楼事件”。鲁迅在日记中记载道—— 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林语堂的不满已经到了临界点。此次风波之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气越来越大,鲁迅觉得林语堂已经无可救药,他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等文章,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
《骂杀和捧杀》 文/鲁迅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 “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 ”借得他一塌糊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 “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个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喳!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糊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