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关于时钟的——但不是那些可以买到、戴在手上或者挂在墙上的时钟,而是在我们的身体里滴嗒作响的时钟。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生物钟不是最近才产生的。体内感知时间的能力不仅人类有,地球上的其他哺乳动物,甚至单细胞动物都有这种能力。这意味着,生物钟对地球上的生物来说一定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对于多数动物来说,如果没有或者不按照生物钟规律活动,就会被其他动物吃掉或饿死。在本书中我将会阐述,违反生物钟规律也会对我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现代的生活方式很少能与我们的生物钟保持一致。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因为旅行而在短时间内跨过多个时区,工业国家里的劳动人口之中有20%的人在做倒班的工作。得过时差综合征的人们充分理解若想使生物钟与头脑达成一致该有多痛苦。即时您不做倒班工作也不坐飞机穿越多个时区,也可能会患上我们称之为“社会时差综合征”的疾病。
一本与“时钟”有关的书当然会涉及时间的问题。生物钟的时间不一定与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需要按时上班、准时赴约、收看晚问新闻和踏上旅途的那种时间一致。社会时间是人们生活用的参照时间。在19世纪以前,社会时间与当地太阳时间是一致的:中午是太阳到达最高点的时间。相当理性的时间划分规则在铁路被发明之后受到了冲击——突然之间人们可以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走过很长的路程,导致当地的太阳时间完全不能用了。旅行的人们几乎每路过一个车站都要调一次时间。因此在1884年很多国家共同实行了一套普遍适用的体系:将世界分成24个时区,把穿过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观察站的经线设定为本初子午线。只要在同一国度(或行政区)之内,理论上人们可以任选一种时间作为社会生活时问(例如中国大陆只实行一种时间,即北京时间)。这本书将会告诉您,不同的时间体系(太阳时间,当地时间和生物个体的内部时间)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您将会了解到,个人体内生物钟产生的时间是如何运行的。这种时间就像身高、瞳孔颜色和个性一样,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同时,也与太阳时间和社会时间有关联。虽然体内时间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时间——比太阳时间和社会时间更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它。每天我们在大约16个小时里都是清醒的,直到我们把活动、思考和愿望放到一边,进入一种像失去意识一样的状态,我们称之为“睡眠”。这种状态的变化每天都在自动地进行,多年以来完全没有人去探究决定这种变化的生物机制。随着日出和日落,动物醒来睡去,植物叶子张开闭合,水中的浮游生物游来游去。所有这些交替变化都在一种生物钟的控制之下,这种生物钟反映了我们这个地球的一天是24小时。但是,睡眠与清醒之间的转换不是两种存在状态的简单转换,不像人们在白天转个身、翻动一张纸片那样简单。两种存在状态更多地是反映了我们所有的身体机能正在进行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包含基因工作的开启与关闭,还有人体组织中持续变换的荷尔蒙与递质的相互作用。
我用了几十年的时问研究决定不同生物钟的机制——从细胞核与蘑菇,到人类。这些研究中,部分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在实验室中我们尝试控制全部的环境因素,例如灯光、温度、食物等;部分是在实际生活中进行的,例如在工厂里,我们测定一天之中的不同参数,或者询问普通人他们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最初我对生物钟产生兴趣,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原因,几乎算是偶然。我们这个专业领域的泰斗之一约根·阿绍夫教授,是巴伐利亚中部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和妻子希尔德有六个孩子,这几个孩子都和我上同一所学校。尽管有年龄的差距,但是我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阿绍夫一家住在阿默尔湖附近的一个叫做埃尔林的村庄,他们的房子在山脚下,非常漂亮,人们叫它“城堡”。阿默尔湖位于上巴伐利亚,离市区非常远,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如果孩子们不断请求,阿绍夫夫妇就会允许他们的孩子邀请朋友们来家里做客甚至过夜。与一大群特别有趣的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十分快乐——所以我能在“城堡”里待多久就待多久。另外,我和教授也相处得十分愉快,因此我对他和他的同事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在17岁时,几乎每个假期,我都会到阿绍夫的研究所做助理。除了能满足我对科学的兴趣之外,还能与有魅力的人们在一起,而且能挣点钱——这真是理想的状态啊!“城堡”的客人越来越多,父母的朋友们,孩子的朋友们,还有很多科学家——有些科学家是世界闻名的,他们经常开展科学讨论。科学一直让我感到兴奋,埃尔林的氛围让我越来越痴迷——这就是我所希望的生活。
虽然在我刚进大学时就比大学毕业生更了解生物钟,我却选择攻读物理学——在我看来,这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根基。但是不久之后我发现,其实我对人本身更感兴趣,而物理对了解人类并没有帮助,于是我转到医学系。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这个专业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因为虽然我希望了解关于人类的一切,但是我的兴趣不在于治疗。后来我渐渐明白,只有了解关于进化、遗传学、生物化学、比较生理学和生态学,才能更多地了解人类。而这些学科不是医学专业的主要研究领域。
所以我最终在生物专业安定了下来。然而多数的讲座课让我感到很无聊。我更喜欢与同学们、科学家们讨论问题,或者阅读大量的科学文献和书籍,这些材料涉及的内容超出了生物学专业第一学年的知识。直到我开始在实验室,工作中搜集实验数据并研究数据意义时,“真正的”学习才开始。把数据以有意义的方式进行阐释,始终是科学工作中让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至今未变。我相信,这种快乐以及探索神秘数据世界所使用的方法,是从我与约根·阿绍夫的交流开始的,那段时间我正处于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阶段。
我在光生物学、神经生理学、大脑研究领域走了几年弯路,后来在“博士后”阶段回到了研究生物钟的学科:时间生物学。在博士后研究的第一阶段,我在埃尔林与约根·阿绍夫一起工作,此时我的身份不再是大学生,而是(某种程度上)独立的科学家。直到1998年10月他去世之前,我和这位“老头子”(家人和好朋友都这样叫他)一直是互相信任的同事和亲密的朋友,他也一直是我的导师。与阿绍夫共事的两年里我主要研究人类年周期,在那之后,我依然想深入研究生物钟在细胞里是怎样起作用的,它们在分子的帮助下怎样规定体内的“一天”。因此我们决定与当时另外一位时间生物学领域的先锋人物哈佛大学的伍迪·哈斯廷斯教授一起工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我在他的研究小组里工作了4年,后来几乎每年夏天都回到那里。
最终回到德国之后,我发现那里的学术氛围不太适合研究人类和单细胞海藻的科学家落脚,尤其是我这样的科学家更喜欢对新领域(例如生物钟)感兴趣,而不是在狭小的专业领域中。我属于哪一种德国学术群体呢?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人类学或者医学?最后我到了医学系——那里恰好有医学心理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之所以成为我的学术故乡,是因为所长埃斯特·波珀尔。他是我在德国遇到的少数对新领域、对时间相关的领域感兴趣的人之一,并且他不仅仅对研究样板有机体感兴趣’。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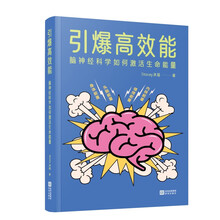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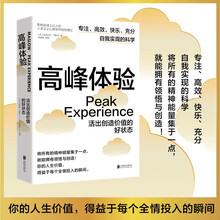
——牛津大学罗素·福斯特教授
通过《神奇的人体生物钟》,蒂尔·伦内伯格这位慕尼黑路德维希大学的教授带领读者探索了这片神秘的未知领域。蒂尔将人们比喻为“云雀”或者“猫头鹰”,他解释了时差综合征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青少年早上总醒不来……蒂尔是一位充满智慧的向导,拥有将尖端学术变得浅显易懂的能力,这本书是这个重要新兴学科的重要著作,无论是致力时间生物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仅仅想弄明白“为什么我的睡眠总存在问题”的普通人,都可以一读。
——《怪诞心理学》《正能量》作者理查德·怀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