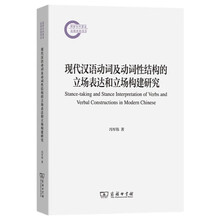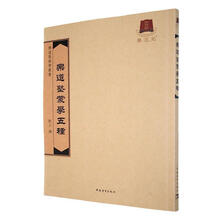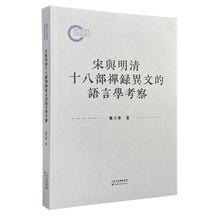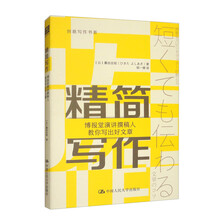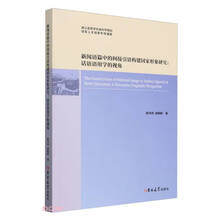从情境脉络中抽绎、归纳。知识的建构是认知主体在情境脉络中生成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知识具有适应性,与形成知识的情境脉络相关联。“概念、模式、理论等能证明它们对于自身被创造出来的情境脉络是相适宜的,那么它们也具有生存力。”情境脉络由情境组合而成。情境是知识的源头,是知识的土壤,是知识的家园。知识从情境脉络中抽绎出来,成为概念,由许多概念构成系统性知识。这些概念和系统性知识只是暂时离开情境脉络,其背后还是有情境脉络的。只有当它们回到情境脉络中,才具有生命力,如果永远离开情境脉络,就很容易枯竭而亡。而认知就是认知自身与情境脉络相适应的活动,因此不能停留于体验世界,而要把认知看作是一种理解、建构概念的行动方案,它超越当下体验的世界,扩展到我们体验世界时所追求的共同认可的概念结构。
因此,建构主义者相信知识真正生成之前,对新情境(对语文学科来说即语境)进行解释、反复讨论问题、思考分析、总结等,对知识的形成都是很有用的。知识建构的起点在情境中,教师要为学生提供加工和运用新知识的情境,学生必须详细解释、质疑所面对的新情境中的问题。在情境中分析新内容和已经学习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把新知识与已有的知识网络联系起来,把新内容与学生的已有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想象、预测、推断他者的认知。如何确定认知主体构建的知识符合社会普遍认可的规则,这是建构主义者始终面临的关键问题。于是又要绕回到这个问题上:如果所有知识都是认知主体自己建构的,那么一个人如何理解他者?反之亦然,他者如何能够理解“我”?这就要求认知主体能够进行“他者”的建构,达成与“他者”的一致性。建构主义者尝试建构解决这个问题的模型,欧内斯特·冯·格拉塞斯菲尔德以康德《纯粹理性的批判》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的模型。康德写道:
我们只能通过将自己的主体性注入到其他人的实体中,才能想象其他主体。为了形成在经验环境中具有生存力的行为方式,孩子学习对自己的建构对象进行预测。……如果你想抓的蜥蜴看到你,它就会逃开。要了解这一点,你必须将视觉能力注入到蜥蜴身上。你所称呼的“爸爸”的实体将会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会伤害你自己。考虑到这一点,你必须将一种预测能力注入给你的爸爸(以及像他那样的其他实体),即与你所使用的预测能力相当甚至超过你的预测能力的实体。这样的话你就能超越你自身的要素来建构“他者”,这些他者也随即促进你自己的想象。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借助想象、预测、推断来理解“他者”,解释“他者”与我们发现的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是如何依据我们的主观经验以概念方式被建构出来的。
其实这类建构是东方人所擅长的,在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中经常能够看到。下面摘录了教学老舍的散文《想北平》时,三位学生在课堂上交流的阅读体验:
生1:“真”字,朴素、简单,但又缺失不得:这是诚挚的爱的表达。蜻蜓和塔影,也固然是极为渺小的片段,而一种赤诚的爱却使这种感情升华到了更高的地方。说不出的,最终吐出来,掩不住、道不明的,对母亲的爱也和它一样深沉。记忆是点,时光是线,这座城是面,而爱将它们拼合,深入心灵的空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