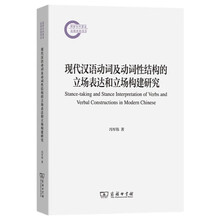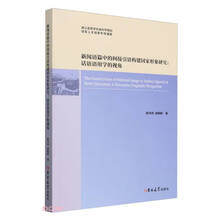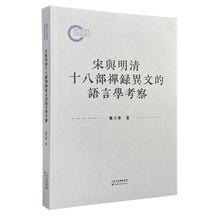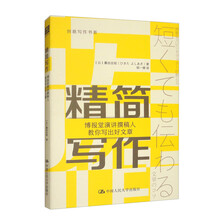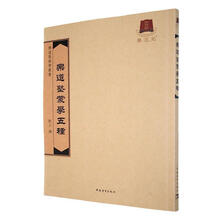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及这段对话,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在探讨一个奴隶所掌握的几何知识究竟有多少,而是记录了人类历史上也许是最早的一次对于知识的本质的反思:知识从何而来?由什么组成?在人的心智中以何种方式再现?我们从中甚至可以窥见一个关于知识的理论雏形一不管它正确也好,错误也好。
从这个对话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按对话所录,也当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最纯粹的知识是数学及其引发的相关学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仅能偶尔捕捉到最纯粹的知识的一点影子。柏拉图还认为人天生就拥有理解各种几何知识乃至所有其他知识的能力,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将这种与生俱来的潜在能力激活。
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中,古希腊人对于探究知识本质的热情一直影响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在整个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那时探讨知识的本源是神学家的专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继续着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开始从新兴的实验科学的发现中汲取养料,比如笛卡儿、洛克和康德。到了19世纪末,新的学科和新的哲学流派不断涌现,其中不少都声称以探究人类心智的奥秘为主要目的。
今天,新一代的认知科学家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循着新的视角,仍在试图解答2500年前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困惑的问题:什么叫做有知?什么叫做无知?什么是正确的知识?什么是错误的知识?大致说来,认知科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有两个,一是被人类所认知的,即外部世界中的客体;二是认知外部世界的人,包括人的感知系统、学习机制、记忆和理性等。知识的本源是什么?知识怎样被存储?怎样被标注?又怎样会丢失?聪明人与蠢笨的人之间有怎样的差别?什么样的人学习起来得心应手?什么样的人学习特别费劲?儿童怎样习得知识?原始部落的成员、脑部受伤的病人以及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科学家之间在习得知识方面会有怎样的不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