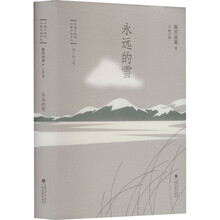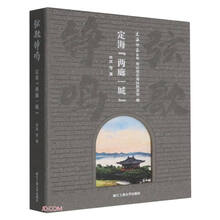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江南物事》:
云片糕曾经,云片糕代表一种很有高度的幸福指数。很稀罕的甜,很有层次的蜜,这甜蜜里尽是盼望和梦想。
小时候,我就是这样盼望和梦想着拥有堆得很高的云片糕,像山,可以随意取之、食之;放嘴里,融了、化了,回过味来,满口生香,浓得化不开。事实上,这种感觉,多半是在梦里。
如今,云片糕是我对旧时江南的一份记忆,偶尔回望那些时刻,捡起曾经的片断,总带着苦涩的甜蜜,超脱现实的想象。这一切是真的吗?那样的过往,是我所经历过的吗?我一直固执地喜欢“云片糕”这个名字,它常常让我产生许多联想:比如洁白的云,一片一片;或者是飞扬的雪花,也一片一片。
我也喜欢它的包装,很质朴,又很喜气。通常做成十几公分长、五六公分宽的长方形,大小适中,正适合握在手里,很称手。
白纸、红字,上书“白糖云片”、“松子云片”、“核桃云片”、“芝麻云片”以及“高桥食品厂出品”、“骑塘食品厂出品”等字样,质地、厂址一目了然,就像乡下的蓝印花布一般,耐看又亲近。
最要紧的是它的内聚力。上好的糯米、纯粹的白糖做主打,松子、核桃、芝麻助阵,再加上祖传秘方调制,方能做成上等的云片糕。若是刚刚出厂,拎到手上,重甸甸,打开包装纸,但见薄如云片,自如丝绵;摸上去柔软又有韧性;吃起来,则细腻如酥,入口即化——云片糕的名字就这样有了名副其实的担当。
中国人向来崇尚礼尚往来。云片糕好看、好吃,但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礼节,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江南农村,曾经风行,风行到似乎没有云片糕的新年,不口L{新年;没有拎着云片糕做客,就算不上做客。世间万物皆有存在的理由,云片糕也自有其风行的理由。“糕”,谐音“高”,民间最朴素的信仰与期望,便是日子红火,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好口彩啊。小小云片糕,就大有深意了。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母亲将堂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八仙桌擦得亮亮。桌上放着长生果、瓜子、番薯糕之类的茶点,静待来客。客人来了,将一包云片糕放到八仙桌上。母亲便客气一声:“来就来,还拿东西?”“没哈啊!”客人一笑,在八仙桌旁落座。母亲即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镬糍糖茶,主客寒喧,其乐融融。
大人闲话之间,小孩便把眼光凑上去看桌上的云片糕,小眼睛一瞄,便确知是何种云片,是高桥食品厂还是骑塘食品厂出的,若是前者,当然比后者更好吃,空自窃喜。高桥糕可是有名的传统糕点品牌,方圆几十里都出名。
客人走了,母亲便收起云片糕,放到房间里的一个大匾中。
小孩们探头探脑望一眼,母亲便会意地说:“下次要做客人的,等客人做完了,再给你们吃。”这些礼物,当然不是小孩子可以随便吃的。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一个新年,大匾里会收到许多糕点,而母亲永远都不会弄错,每一包糕都来自谁家,最后都由父亲带着小孩一家一家去还礼。眼看着这些好吃的糕点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你再渴望也是枉然。云片糕只是一种礼节而已。
而在这来去的当中,新年即将结束,匾里留下来的云片糕多半已经面目全非。包装纸因拎来拎去,变得皱巴巴,掂在手里缺少了分量,拆开纸头,糕已经干燥,窸窸窣窣地漏下来。虽然没有了先前的柔软韧性、细腻如酥,但甜香依然。扳一片放进嘴里,或者用热水泡了吃,搅拌成米糊,就像西湖藕粉的味道,仍然吃得津津有味。当然,那只是在二三十年前的感觉。
除了过新年做客,糕点先行之外,那时在江南农村,还有许多传统习惯,平时看病人、走亲戚、办喜事必用糕点,小孩子第一天上学校,新人头次上门做客,造新房子上梁,也都离不开糕点。
上学称结缘糕、高考称状元糕、造房称上梁糕,各种称谓,名目繁多,好口彩,图顺经,广结缘,好多意味在里头。后来,条件好一点的,做客还加上各种各样的饼干盒,包装好看,也不易碎。
今天,再也不时兴拎着糕饼做客,那近乎寒酸的行头,早已过时。各种大礼包、滋补品登场,一个世纪转身,历史就这样翻了过去。云片糕美好而无奈地定格在了上个世纪。趁父母不注意,我们偷吃云片糕的美好感觉,也彻底成为过去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盼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我们,小时能吃到云片糕,就是天大的幸福。一想起云片糕就嘴馋,那种吃到嘴里甜到心里的感觉,如今的小孩子是无法体会到的,甚至听到了会觉得好笑。也难怪,如今什么都有了,还有哪些东西让今天的小孩子去盼望呢?无疑,云片糕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如今已慢慢远去。幸而在我们老家,还有一家专门制作这种核桃云片糕的手工作坊,成为寂寥的最后守望者,依然在延续着我旧时的梦。
也幸而还有少数依然钟情于云片糕的人,特意要到那里定做这样的云片糕来吃。即便那仅仅是怀旧,也足可安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