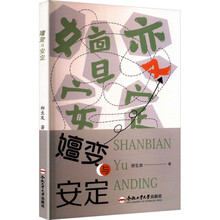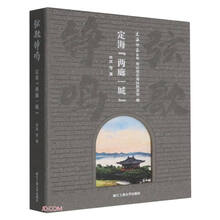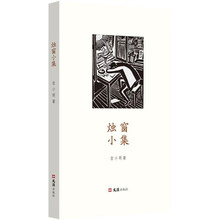[精彩试读]
自序
关于死亡
在西藏,我学会的第一件事,便是面对死亡。
2012年,我从西藏飞去广东奔丧。我以为在藏多年,已储备了足够的无常和生死观,我以为我随时准备好迎接每一个亲人的死亡。可是死亡一旦来临,瞬间瓦解一个人多年来的修行。我要送走的人,是我的爷爷——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风琴师。
一阙棺木,安放了一个天国的梦想。两万多个破碎的日子,连成一生。经亲人的泪水泡浸。入葬。化为泥土,重回耶稣基督的怀中。人生之须臾,身体所容纳的,不过是半间房屋的粮食,两担喜悦与苦痛,一阙等量身高棺木,就可以忍耐,卑微地熬过一生。
他存放于冻床,零下十六度。停尸数日,接收鲜花、泪水、歌声和祷告。但还是有那么一瞬间,我确信他还活着。落寞而修长的背影,灰白色长衫,手指跳跃在琴键上,日暮长廊里站立良久,在藤椅的摇晃里睡着,烟灰被风吹散,落了一地。
三天的葬礼,我读完了一本《圣经》。读到这段:“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圣经•传道书•人生的虚空》。死亡,是每个人最终都要履行的程序,接受不接受,它都会如旧来临。盖棺的时候,爷爷头枕的不是泪水,也不是回忆或金饰银器,而是平日他那本翻至皱巴巴的《圣经》。我们祷告、唱诗, 欢天喜地将他交付于天国里的耶稣阿爸。我看见出生与死亡恰好连成一个圆,且天衣无缝,没有任何破绽。这个圆圈,是开始也是终结,它指向两个方向。当出殡的泪水淹没整座山头,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刺破黎明。
当最后一抔土,淹没你忧伤的头颅。耶稣会将你重新埋进土地,像出生时那样洁净。从此风雨雷电受你差使,春夏秋冬都听你命令。
最后,神在你的墓碑上刻下:农民、基督徒、风琴师。
关于爱情
在西藏,我学会的第二件事,便是面对爱情。
那些挫败的爱情,最终让你知道,有些人今生与你纠缠,是来索债的。每一次都爱得缠绵悱恻、头破血流。最终这些爱人,都成了生命里的匆匆过客,原来你不过是一个中途驿站。
曾经为了一个男人,离开西藏。变卖家当,卷席所有,去往他的故乡。这是除了西藏,第二次背井离乡。女人最容易相信的是爱情,同样也最容易被爱情伤害。半年平静的生活,终于在子夜里抖出所有密谋的背叛。
最终,西藏收留了孤独无依、狼狈不堪的我。我回到西藏,将自己安置在拉萨河畔,像当初决绝变卖家当一样,重新布置生活。命运无常,生活很荒诞,每个人都是荒诞的旁观者,又是荒诞的承受者。你不得不暗笑曾经有多么无知和轻狂,竟相信爱情所向披靡,是最坚固的依靠。
很痛苦的时候,我曾经问禅师,如何才能放下。他给我一个白瓷杯,让我承接他倒的开水。水溢满,烫到我的手那一瞬间,白瓷杯摔碎在地。我看着发红的手指,沉默片刻。清风吹起杨柳枝,拂面温暖。拨开柳枝,禅师已在水中央,渡船而去。他没有与我告别,人世两相忘。晨读《佛说四十二章经》中有一句解开了我所有的困惑。“爱欲于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
所有的恐惧,源于我们对爱的渴望与索取。所有的痛苦,都源自我们对外界的攀援执著。有情者未必有缘,有缘者未必有情。爱情,是最无常的一课。而这一课,每个人都经历,却很少人能勘破。
你要等,并且不要期待投入河中的石子的每一次回声。因为每一颗石子都是无情的。遇见那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前,你要准备足够的力量,在进与退之中游刃有余地把持自我。
关于写作
我知道我的艰难,因为我叙述的是西藏。曾经两年的时间里,我没有写过一个字。那时候没日没夜地酗酒、打球,夜不归宿,浑浑噩噩地生活。必须承认,当一个写作者对西藏已经厌倦了猎奇,她便会进入一段灰白的空档期。她不知道何去何从,也不知道如何架构西藏。因为任何人都不具备俯瞰西藏的高度。从物理意义上说,西藏是世界的第三极。除了天堂,我找不到另一个地方能像放大镜观察细菌一样,检验西藏。从精神意义上说,芸芸众生,皆是神灵的子民。我们的灵魂极度匮乏和干瘪,根本不具备与西藏对话的资格。于是,我长时间一言不发。我不知道通往西藏内部的钥匙究竟藏在哪里。
……
八廓街:消失的时间
源起
现在我们所说的“八廓街”,只是音译,准确来讲应该是“帕廓街”。吐蕃王朝初期,拉萨河曾在这一带漫流而过,形成一片沙滩沼泽。松赞干布领臣民疏浚河道,填塞了卧塘湖建起了大昭寺,同时建起了小昭寺,以及几十座庙宇。民居在大昭寺建成之后,引来四方来僧,八面信徒前来朝拜使这里成了传播佛教的中心。随着宗教学校、僧人宿舍的建立,十八家旅店式建筑也应运而生。接着,相应的服务设施、货摊店铺、手工作坊相继出现。随着历史的推演、社会的需要,帕廓街在自然组合中形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街区,几十条小巷曲径通幽,如一条条小溪汇入转经道的主流。这里宫厦套着石屋,阁楼依傍古寺,在庄严肃穆的大昭寺之外,形成了一个人流密集、红尘滚滚的闹市。大昭寺内金佛端坐,净水供奉,香火不断,来自四面八方的朝拜者磕头于此,使大昭寺成为善男信女转经环绕的中心,来自八方四面的商贩也汇聚于此,使帕廓街成为行商坐贾的云集之地。
“八廓”一词,源于藏传佛教徒步转经的习俗。主要的转经活动都是以大昭寺内的觉阿佛像为中心而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转经道有内、中、外三条,内圈即“囊廓”,指的是大昭寺内由三百零八个铜制的转经筒环绕而成的转经道;中圈即“帕廓”,也就是拉萨著名的商业街帕廓街,也是传统上西藏各种物资的集散地;外圈即“林廓”,指的是包括布达拉宫、药王山、小昭寺等在内环绕大半个市区的道路,现在拉萨的林廓西路、林廓东路等名称就是由此而来。藏族人相信,坚持转经可以积累功德,消除业障。转经者通常右手转动转经筒,左手持念珠,口中低诵着六字真言,沿着顺时针方向(苯教徒的转经方向为逆时针)在各个转经道上周而复始,首尾相接地绕行,许多人的肩膀上都挂着像褡裢一样的小白布口袋,装有青稞、糌粑和香草,那是供奉给神佛的食物。
朝圣者
无数个寒冷的夜晚,毫无睡意。而此时,凌晨四点二十分。八廓街一片灰蒙,寒风萧索。使我感觉到了行走时,神灵衣缕中夹杂的复杂经文。脚步似乎有一股潜移默化的力量,将我那颗极不安分的灵魂,领到大昭寺。
朝圣者,是这座城市最早苏醒的灵魂。无论什么时候,白天或是黑夜,午夜还是黄昏,只要我的身体进入八廓街,就会看到一副副起伏不断的身体。他们绕着大昭寺,不断重复的动作,三步一身,意指三步磕一个等身长头。口念经文,双手合十。全身匍匐在地,然后站起来,走三步,再五体投地。磕长头
是藏传佛教信仰者最至诚的礼佛方式之一。 藏传佛教认为,对佛陀、佛法的崇敬,身(行动)、语(咒语)、意(意念)三种方式缺一不可。 磕头朝圣的人在其五体投地的时候,是为“身”敬;同时口中不断念咒,是为“语”敬;心中不断想念着佛,是为“意”敬。
磕长头分为长途(行不远数千里,历数月经年,风餐露宿,朝行夕止,匍匐于沙石冰雪之上,执著地向目的地进发)、短途(数小时、十天半月)、就地三种。磕长头为等身长头,五体投地匍匐,双手前直伸。每伏身一次,以手划地为号,起身后前行到记号处再匍匐,如此周而复始。遇河流,须涉水、渡船,则先于岸边磕足河宽,再行过河。晚间休息后,需从昨日磕止之处启程。短途磕长头,一般是围绕寺院、神山、圣湖、圣迹磕头一周,少则几个小时,多则十天半月。坚持就地磕头也是一种方式,或于自家佛龛前,或于附近寺庙大殿门前,以一定的数量为限,就地磕头。坚持不懈,久而久之,地板、盘石被磨得光可照人。
如马丽华所言:“选择这种苦行的方式,也为了更富有成效地清除今生前世的罪孽,以便无限接近最高理想。”
我希望能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脸,但夜色为视觉设置了屏障。我知道每张轮廓下的线条、肌肉分布,都有所不同。汉族传说里的女娲造人,捏泥成像,每一个人,都是女娲当时的意志之作。意味着不会有完全相同的面孔,而尽管样貌相似,但铸造内心的质地,各有不同。可是,磕长头的人,却打破我所有的设想。
除了能通过直观呈现的身长、年龄、性别的差异之外,我看不出他们的区别。那张不知从何而来的脸孔,只有风尘知道他们朝圣的历史。风尘记录一个人长途跋涉的空间长度,它是每个人身体接触大地,倾听神灵对话的履历。风沙、尘埃随着路途的遥远,不断地聚集。风沙渺小,微不足道。只是谁也不知道,风尘最后幻变成脸上的皱纹,深深浅浅。更像是一条永无止尽、蜿蜒曲折的道路。而岁月始终在其中起起伏伏。对于藏民而言,一辈子若能经历一场磕长头朝圣拉萨,便可洗清身上所有的罪孽。于是,他们成群结伴,十几二十人一起上路。带上锅碗瓢盆、衣服棉被。他们将一辈子积攒下来的积蓄,付诸于一场长途跋涉的朝圣之路。在路上,我看到成群结伴的朝圣者,每次都会停下来。用几句生硬的藏语,询问他们从何而来。而每次临走,不由自主地从包里拿出一些钱,给予这群颠簸流离的人。认识一个中年男子,次仁。已经在路上八个月,从青海而来,一路风餐露宿,食不果腹。不幸的是,同行的哥哥,由于一路掉队,三天仍没有赶上大队人马,次仁放心不下五十岁的哥哥,回头寻找。但寻寻觅觅,不见哥哥踪迹。
后来,发动所有的人寻找,终在一个山崖下面,找到一副难以辨清的尸体。遇上次仁,是从墨脱出来的十月底。当次仁用藏语说着发生在两个月前的经历,似乎所有的悲伤、痛楚,都蒸发在空气里。我对藏语,只是一知半解,无法获取所有的信息。同行的藏族司机,为我们之间的谈话,一字一句地翻译。当最后一个字落音,午后的阳光落在次仁的身体上,他站在那里,异常坚定。他们始终相信,灵神无处不在。尽管哥哥在途中丧生,那是通往了另一条光明之路。
而死亡,并不意味着一切的终结,而是一个转折。因为在宗教世界里,死亡仅仅是一个驿站,人们在此稍作停留,便会匆匆赶往另一个世界。躯体死亡,但精神进入了藏传佛教的六道轮回,等待着一次重生。不,身体也没有死亡。次仁告诉我,他拔下哥哥的一颗牙齿,哥哥始终是与他共同进退。那么,哥哥就不会掉队
了。次仁相信,藏历年前,一定会顺利到达圣城——拉萨。一路磕到大昭寺的佛
祖脚下,才算功德圆满。
大昭寺内宗喀巴大师的神像旁边有一根柏树做的柱子(但有些人说是檀香木
所做,说法不一),这根柱子已有上百年历史,多少人曾经在柱子上留下印记。
穷人肮脏的手指、富人的汗液、鼻涕、牛屎、酥油茶。次仁告诉我,这根柱子被
赋予神圣的宗教的意义,备受仰望。这根柱子被无数经幡、哈达缠绕。细细观
察,竟然深藏着大大小小的牙齿,甚至还有头发、首饰、护身符。对于这一切,
我感到疑惑。为什么要在这柱子上,塞满这些东西?我想起路上遇见的朝圣者次仁所说的一番话,即使哥哥不幸途中遇难,亦要把哥哥的牙齿带上。莫非就是为了放置在这根柱子里?经过一些专家的证实,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柱子里塞满了死者的牙齿、遗物,我们无法理解其中的原因所在,藏民族虔诚的宗教信仰意识决定他们所做的一切。因为实现信仰的场所,并不在于看得见的具体所在,而在于一个人的内心。用一颗牙齿来还毕生志愿,代价是付出了生命。牙齿的分量,看似微不足道,但包含着的却是一个生灵在尘世中留下的唯一痕迹。
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博士的文化模式理论,将汉民族的文化模式理解为现世主义,而将藏民族的文化模式理解为来世主义。“在藏民族社会中,今生现世当然重要,但相当程度上,它是为了来世的存在和过程。”藏民族与汉民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二者的思想维空、意识常常不在同一个维度上。于是,我们很难切身想象藏民族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磕长头,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更应该是一种状态。是身体五体投地和精神上高度集中的状态。这个词,作为过客,我们所看到只是单纯身体赋予的动作意义,而藏民族却为此付诸一生。
藏文的“身体”是“Lu”,意思是“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就像行李。每次提到“Lu”都提醒我们:我们只是一个旅者,短暂地寄居在这个肉身。西藏人不会把时间花在追求舒适的生活上来困扰自己,只要够吃够住就满足了。
缘起缘灭
我曾去过那受光最多的地方看到了回到人间的人们,无法也无力重述的力量
——《神曲—天堂篇》
文人墨客形象地把八廓街比喻为时钟,大昭寺为时轴,而转经人,朝佛者则构成了时针。走进八廓街,如同走进一个圆形时间。这是一个取消了时间性的时间,即日升月落,春夏秋冬,生死轮回,都呈现出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状态。
常常看到无数朝拜者,在大昭寺门前原地磕头,嘴里念念有词。“咒语是一些神圣的声音,一些听觉符号。它没有具体的含义,但是像音乐、诗歌的音调、韵律一样。能够唤起内心深沉的感情,超越思想,以及日常语言的日常形状。对于入门者而言,以一种非常直接、坦诚的方式背诵真言,能够唤起内心中潜在的力量。而对于其他人,它依然处于一种神秘状态。若没有充分的准备和精神状态,只背诵咒语也无济于事。因为咒语的声音,不仅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这种真言必须在意念里产生,让心灵倾听。”
八廓街的循环时间,体现在藏民每天沿着八廓街大昭寺顺时针方向转一至三圈。八廓街如一个旋转着的大磨盘,它带动着每一个进入这个“场”的人,按顺时针方向行走。 “凌晨里踩着露水走上街头的就是那些城市里最早起身的转经人,整个城市在雾气笼罩的寂静中还没醒来,站在通往大昭寺的大街西头,就能听见刚刚转弯入东头的转经人行走传出的朦胧脚步声,他们多半是上了岁数的人。早醒的狗喜欢窜出来对发出的声音或显出黑影的地方狂吠几声,但从来不伤人,我也成了它们打招呼的对象。等我理解了拉萨凌晨的秘密,走在无人的街中心不再恐惧黑暗的沉寂中突发的任何声音时,自己也像一个平静而专注的转经人。”巴荒在《阳光与荒原的诱惑——巴荒的西藏心灵史》中这样写道。
1936年到过拉萨的英国人斯潘塞•查普曼,在他的《圣城拉萨》一书里写道:“拉萨城本身很小,真令人感到惊异,建筑物前的小广场周长只有2英里……
大昭寺是全藏朝圣的最圣洁之地”,“当一缕阳光在布达拉宫金色屋顶上闪烁时,你会激动不已”。藏民在八廓街进行的生活内容,除了与我们一样,完成吃喝拉撒等生物学法则之外,更多的时间便是磕头、念经、晒太阳、冥想。原地磕头,藏语又称“恰差”。我认识一个从青海而来的康巴阿佳,每天在大昭寺原地磕两千个头以上。拉萨的冬天,夜幕的脚步来得比夏日紧促,有些迫不及待。晚
上十点,当八廓街所有的商店、摊点已经陷入沉睡状态,路过大昭寺,一眼便能
瞥见阿佳那张被寒风刮伤、倍显通红的脸庞。一副消瘦的身子,却有着一股常人难以想象的能量,抵抗着来自体内的饥寒。她站立在大昭寺明灭的灯光里,犹如一座日夜坚守在海上的灯塔。我记得,最晚遇见阿佳的一次,是深夜十一点。大昭寺门前磕头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她依旧在。我走过去与她打招呼,她见是我便热情地微笑,然后用她那无数次摩擦过大地、布满茧子的温暖双手,握着我异常冰冷的手。我与她的对话,很多时候并不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上,而是手势和笑容。我们语言不通,但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我生涩的藏语,让我这个平时在人前滔滔不绝的人,顿感失语受挫。阿佳说,她每天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点,都在大昭寺门前磕头。日复一日,形成一种不得不延续的行为习惯。她几乎是所有在大昭寺磕头的信徒中,最为“夙兴夜寐”的一个。她的生活保持某种恒定状态,具备军营里的节奏性。
对于她而言,时间似乎无关紧要。她用一辈子做赌注,为了一场不知道是否有回报的来世。而时间于她而言,又似乎有着某种苛刻的对待。起早贪黑地磕头,从不迟到,时间把握得刚刚好。科学的精打细算,也无法如阿佳那般对时间流逝具有的敏锐感知。
我与她的时间,刚好颠倒错乱。往往她从梦中起来,进入磕头的修行功课,我才觉出丝许倦意,进入梦乡。当她沐浴在阳光下喃喃自语,而我的生物钟正转入黑夜状态,打着疲惫的呼噜。当她以最后一个虔诚的膜拜来告别一天,躺在床上,很快陷入熟睡状态,我,才刚刚进入书写状态,我的生物钟显示的是白昼,是我的精神集中的最佳时间。于是,我与她似乎游走在时间的两极,彼此对时间的看待,南辕北辙。或许,当我以为我活在现世,活在工作的意义价值之中而沾沾自喜时,藏民则以一种悄无声息的安静状态,履行着对自我精神和对神灵的皈依诺言,他的身体虽具备现世的物理意义,但精神早已超脱今世的阈限,朝向来世。但这一过程,我们无法窥知,灵魂是否朝向今生来世。俗话说眼见为实,在物质事实的领域内,这个标准基本上是成立的,但在精神价值的领域内就完全不适用了。理想、信仰、真理、爱、善这些精神价值永远不会以一种看得见的形态存在,它们实现的场所只能是人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人的内心有没有信仰,这个差异必定会在外在行为中表现出来。可是,差异的根源却是在内心,正是在这无形之域,有的人生活在光明之中,有的人生活在黑暗之中。
大昭寺的灯火,是最早燃起,也是最晚熄灭。而灯火的燃起和熄灭,寓意着人生的两大哲学命题——生与死。在这里,婴儿出生后过一段时间,就会被大人抱到大昭寺拜佛,称为“头次出门”。而人死后,家人会到大昭寺的释迦牟尼佛像前,敬献死者的姓名,供灯、哈达,以及回向礼,祈求佛祖为死者超度亡魂。
遗体送往天葬台前的某天凌晨在引香队伍的引导下,由专人将遗体背到大昭寺门前,进行最后一次祈祷,大昭寺的门廊下会留下一条哈达和供灯。然后围绕着八廓街转一圈后,遗体才被送往天葬台。于是,对于藏民族而言,他们的生与死,都与大昭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八廓街,穿透着藏民族一生。既是生命的必经起点,又是生命完结的终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