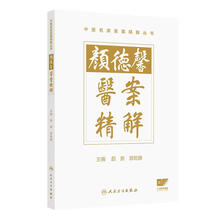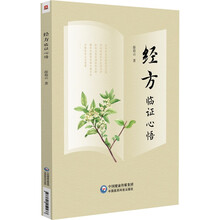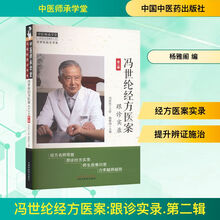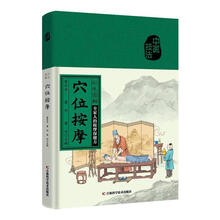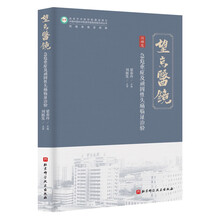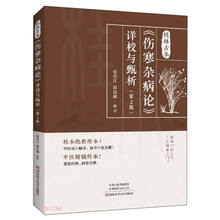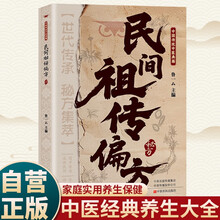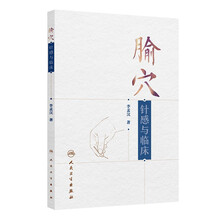《韩世荣皮肤病临证实录》:
二、取象此类法在皮肤病临床中的应用
韩老师认为取象比类是中医的精髓所在,该法渗透于中医疾病命名、四诊辨证、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以及中药功效等诸多方面,常常使临床辨治别开生面。
1.确定病变命名
在中医皮肤病命名上,也常根据皮疹的形态、部位等特点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进行诊断命名。如皮肤迅速变赤、状如丹涂脂染的“丹毒”,皮疹发生于面部两颧、形如蝴蝶且呈红色之象的“红蝴蝶疮”,小腿部多个结节沿腿部血管排列的“瓜藤缠”,以及疮起攻窜作痛且状如蛇形的“蛇串疮”等。其他如水痘、黄水疮、臁疮、鬼舔头、蝼蛄疖、蚂蚁窝、白癜风、蛇头疔、对口疮等等,也都为取象比类的方法命名的结果。
2.类推病因病机
《内经》按照“人与天地相应”“阴阳五行”以及“经络学说”等思想将人体自身,以及人与社会和自然界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探究人体生理病理及辨治内容。韩老师认为,皮肤居于人身之表,而为一身之藩篱,皮肤病症的产生,内则与五脏、七情、饮食五味等相关,外则与六淫、气候、环境等密切相关,故通过取象比类的方法,常常能够较容易地推知其发病的原因和机制。
如自然界中,五行之中,土能制水,水失土掩则横行肆虐,而在五脏,脾为土脏,脾虚生湿;凡置阴雨之时,或阴暗、低洼、闭塞之所,则常湿气氤氲,比之于人,则湿邪留恋之处,常有脾阳郁遏之机,症见脘腹胀满,肌肤肿胀,便溏少尿等,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所说:“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周易·乾》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内外湿邪均属阴邪,内湿即生,则易与外湿相招,抟结肌肤而发为皮肤病症;湿性重浊黏腻,湿性趋下,故可推知湿邪伤人易袭阴位,临床凡见皮肤病变在身半以下或四肢末端,病情缠绵难愈,或伴有头重如裹、身体困重等患者,每多湿邪为患,如《素问·太阴阳明论》云:“伤于湿者,下先受之。”水满则溢,湿邪偏盛,外渗肌肤而见肌肤肿胀、水疱、渗液,痂皮厚浊、鳞屑污秽以及皮肤多油等症;湿浊上泛,现于舌则见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白或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均可通过取象比类法而互推因果。
《灵枢·本脏》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望诊遵经·五色相应提纲》亦云:“尝考《内经》诊法,以五色行于外,五脏应于内,犹根本之与枝叶也。”韩老师认为,皮肤病常形于表而多源于内,通过观察皮肤黏膜以及毛发等的异常,常常即可推知其相应的内在病变。如脾开窍于口,推知口唇病变常与脾胃运化失常有关。
3.制定治则治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明确强调中医的治法确立需要进行同自然界事物运动取象比类的过程。在《内经》基于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记述了许多朴素而经典的治法,如“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等。经后世医家的不断发展,创立了“提壶揭盖”“增水行舟”“围师必阙”“釜底抽薪”“扬汤止沸”“欲求南风,需开北牖”等治法,丰富了中医的临床治疗思路。
临证中,韩老师善于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制定治法,颇能启发后学。如针对邪气致病,认为应以祛邪为第一要务,但又强调必须“给邪出路”,使邪去正安。譬若贼匪来犯,当开门逐寇,而不可闭门缉盗。至于如何给邪出路,则当因势利导,常用者有三种途径:汗及二便。其中汗法在皮肤科临床较为常用。韩老师谨崇“其在皮者,汗而发之”之意。临证见风寒或风寒湿邪袭表者,每以麻黄、桂枝之辛温宣散,大开鬼门;表风热郁表者,辄以金银花、连翘、浮萍辛凉轻清,发散透表。若病久邪气深入,瘀结脉络,致去路不畅,则宜活血散瘀、宣通脉络,使邪气易于消除,药如赤芍、丹参,或如川芎、红花,或如威灵仙、忍冬藤,甚或全蝎、蜈蚣等;对于邪气难以速去或去而复至者,若属正虚邪恋者,则攻补兼施,逐邪外出,如我强敌弱,贼自闻风丧胆,不战自溃;若因内外邪气相搏,如贼匪潜伏不去,必是有恃无恐,有险可依,治疗时则当视邪之所依而用药。如无形热邪与有形之痰湿、瘀血、食滞、宿便等邪相搏,则应根据辨证去其有形之邪,使热无所依而易散。
再如,论及阳气的重要性时,韩老师常引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之语予以论述。在治疗硬皮病、银屑病、冻疮、寒冷性多形性红斑等病,症见喜温畏寒,四肢清冷、小便清长,舌淡苔白、脉沉细微等,辨证属阳虚寒凝者,常用附子、干姜、肉桂、麻黄等温阳散寒,乃取自然界“离照当空,阴霾自散”之意;又取自然界阴阳相生之理,佐养阴之熟地、白芍等,使“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还常伍以健脾补土之甘草等,则又恰合“灰能伏火”之意,如郑钦安《医理传真》曰:“如今之人,将火煽红,而不覆之以灰,虽焰,不久即灭;覆之以灰,火得伏,即可久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