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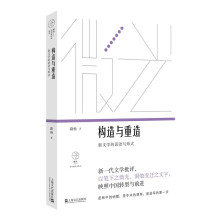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侵袭,性别、种族和民族,不仅对于英国民众成了必须面对的主题,而且成了全人类的重要议题。在这本探讨英国著名当代小说家朱利安·巴恩斯小说的学术专著中,我们得以从文本细读中,领略观察敏锐的小说家是如何捕捉、解读、分析这些主题的。我们会随着巴恩斯的观察,去思考:女性气质、男性气质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性别与性向是否是流动的?种族特征是什么?民族性是什么?涉及小说包括《福楼拜的鹦鹉》、《10 1/2章世界历史》、《地铁通达之处》和《英格兰,英格兰》等。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是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在他从事小说创作近40年的时间里,西方社会的身份政治运动频发,身份因此也成为巴恩斯小说不可避免的主题。巴恩斯的身份书写主要包括性别、种族和民族等多重维度,体现了他与相关社会政治文化和传统的对话,既是对身份的反思,也是其“身份政治”的表达,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
前面探讨种族身份时,提到西方身份的自我表征离不开东方。同样,想象英格兰民族身份也离不开他者参照。托什(John Tosh)指出,“认同,尤其是本身具有不稳定因素的认同,常常都要依赖一个被妖魔化的‘他者’的在场,‘他者’具备所有与自我所渴望拥有的那些优点恰好相反的特征,而且总是依附于现实生活中最近的人身上”(Tosh 49)。对于英格兰而言,这个“最接近的人”无疑就是法国。
巴恩斯在接受采访回答英格兰人现在的含义时,也表明了法国就是英格兰的外部参照,他说:
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能否找到答案,因为关于英国的(the British),尤其是英格兰的(the English)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弄不清英格兰人的含义。不,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缺乏想象力;部分原因是这个事实,即他们以世界最强民族的身份度过了两百年,或者多长时间。如果你们是世界上最强的民族,就像你们看到现在的美国,你们也不会很清楚你们是什么。你们认为你们是规范,其他民族是规范的一种变体(a variant form of what is the norm)。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一直以英格兰人为参照定义他们自己,而英格兰人(the English)则不知道以谁来界定自己。他们不知道是否法国人是参照——常常是法国人(笑了一下)——有时是德国人,虽然在不同时期我们既非常接近于法国人又非常接近德国人。(Fraga 141)
在这里,巴恩斯表明英格兰人不会以苏格兰人、威尔士人或爱尔兰人作为外部参照想象自我,因为它们不够强大,而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则不同,它可以对英格兰形成威胁:英国兰性由于威胁的存在而引起,也因之而持续(Westcott 9)。同时,从巴恩斯的话里还应该看到,现在并非整个英国都以法国为外部参照定义自身,因为苏格兰、威尔士以及爱尔兰是以英格兰为外部参照对自身进行界定,只有英格兰以法国或德国为外部参照定义英格兰民族身份。
在小说中,巴恩斯主要以法国为参照界定英格兰性。巴恩斯每一部小说均含法国元素,涉及法兰西文学、文化等方面,而且法语也堂而皇之地直接出现于几乎每部小说中,这些成分在语言、思维、意识、文学、审美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与英格兰形成对比,成为其想象英格兰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参照。
在英格兰传统界定自身确立起来的二元对立中,法国性总是劣等的一方,而英格兰性表示美好:英格兰是善,法兰西是恶;法国人粗鲁、暴乱,英格兰绅士而克制。巴恩斯小说也将英格兰性的反思建立在英格兰与法兰西对立的基础之上,但这种对立并不是出于恐法和贬法的心理和认识,而主要是试图站在法国一方,借助法国文学和文化对英格兰性进行思考,他的思考不是自我褒扬,而是对自我的批判,英格兰性往往由低劣来表征,而法国性以优越来展现,无论从语言、文学,抑或从礼貌礼节和审美观之均是如此。
与法国人相比,英格兰人是冷淡的:在小说《英格兰,英格兰》中“冷淡”在英格兰性的前五十位排名中,名列第二十一位,是英格兰民族特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巴恩斯对英格兰人的冷淡颇有微词。小说中“英格兰,英格兰”与老英格兰的封闭不同,它突破了老英格兰的封闭和狭隘,主动与国际进行接轨,人们冷冰冰的态度得到改善,巴恩斯写道:“在这里,你将感受到国际上的那种友好,而不再是传统冷冰冰的英格兰式欢迎”(184),“你是愿意成为那个困惑的人,顶风站在肮脏的老英格兰城区的路边,试图弄清该往哪儿走,而其他人流从你身边擦肩而过,还是成为被关注的对象”(184)。与此相反,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巴恩斯引用G.M.马斯格雷牧师的话赞扬法国热情而贴心的服务品质:“我们的朋友G.M.马斯格雷牧师十多年前在布洛涅下车的时候,被法国铁路运输深深吸引住了:‘行李的接收、称重、标号以及费用支付设备简单而完美。每一部门都有序、准确、守时。礼貌又舒适(在法国舒适!),每一种安排都让人感到愉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帕丁顿那种到处可见的喧嚣或混乱中进行的;更不用说那里二等车厢差不多可与我们头等厢相媲美了。情况竟然是这样,英格兰[英国](England)真是无地自容哪!’”(140)马斯格雷牧师还认为“法国海关官员的行为像绅士,彬彬有礼,而英格兰[英国]海关官员(English customs officers)是无赖”(133)。
法国人的热情友好在《生活的层级》中尤为突出。该小说分为三个部分:“高度的罪”,“在地上”(“on the level”)和“深度的缺失”。第一部分是关于人类最早的热气球飞行尝试以及热气球飞行者们的感受,属新闻和史料性质的文字;第三部分是作者告白亡妻带来的痛苦以及相关的生活变化,有传记的成分。第二部分是真正的虚构故事。作品延续了巴恩斯的一贯风格——将虚构与真实,将小说与其他文类混杂在一起。在虚构故事的部分,男主人公弗雷德和女主人公莎拉上演了一场无果而终的爱情剧。他们是小说第一部分的热气球飞行者,是历史真实人物,虽然他们同为人类最早的热气球飞行者,但并不相识,更没有相爱过,巴恩斯虚构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因为“他想看看将两个从未在过一起的人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在第一部分的早期热气球飞行记载里,皇家卫队上尉及飞行协会理事成员弗雷德·伯纳比对法国人的热情和善良深有感触。他1882年从英格兰的多佛煤气厂(Dover Gasworks)起飞,在法国的蒙提尼城堡(Chateau de Montigny)附近着陆时,当地人跟着热气球看热闹,一个农民不小心遇到了危险,“他的头陷进了半瘪的气囊里,差点窒息过去”(7),好在大家很愿意帮忙,不仅挽救了险情,还“帮着折叠好气球”(7)。伯纳比“发现这些穷困的法国农民比英国人更善良,更礼貌”(7),而且好客的农场主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过夜,农场主的妻子还准备了丰盛的晚餐;之后村里的医生赶过来,屠夫也来了,还带着香槟酒。席间,“医生提议为共同的兄弟情举杯”(9)。虽然“作为英国人(being British),他向这些法国人解释君主立宪比共和制优越”(9),但法国人的热情好客让伯纳比感动不已,他不得不承认“热气球在诺曼底着陆确实比在艾瑟克斯好”(7)。
与法国人相比,英格兰人缺乏艺术品味。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叙述人布莱斯怀特这样描述英吉利海峡两面的不同天气状况和景色:
从法国那边望去,海峡上的天空的光线完全不相同:更加清晰,但更加富于变化。天空就是一个蕴含着无穷变幻的剧场。我并不是在浪漫幻想。沿着诺曼底海岸有不少艺术馆,进去看看,你会发现,本地的画家一遍又一遍地画这样的景色:那北边的风光。一片海滩,大海,还有变幻无穷的天空。拥挤在黑斯廷斯或马盖特或伊斯特本的英格兰画家[英国画家](English painter),眼睛盯着性情乖戾、单调乏味的海峡,从来画不出类似的景象。(102)
这不仅只是对两岸不同风景的描述,也是两个民族性格的写照,它区分法国人的浪漫气质和艺术修养与英格兰人的沉闷、乏味和呆板以及无艺术秉性的特质。小说中马斯格雷夫在法国看到的蓝色正是法国浪漫性格的写照:“在卡昂,马斯格雷夫看过一次赛舟会……大部分观众是男人,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农民,他们穿上他们最漂亮的蓝衬衫。整体的效果就是一种最漂亮的淡蓝。这是一种独特的很正的蓝色;……法兰西的颜色”,“男人的衬衫与长袜是蓝色的;四分之三的女人的外衣是蓝色的。马厩与鬃饰是蓝色的……”,法国比他熟悉的“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所拥有的蓝色都要多”(117)。在《生命的层级》里,巴恩斯写到:“这些热气球飞行者很惬意地遵从民族的陈规”(6),所以,英国(British)飞行者伯纳比体现自己是“一个实用的英国军官(English officer)”认为“自己可以应对”(6),拒绝法国渔船让他在海上降落的信号。相比较而言,法国飞行者萨拉的飞行却充满浪漫气息。她和他的艺术家情人以及一个专业飞行员一起乘坐热气球,途中他们“打开一瓶香槟”并“把盖子点燃,抛向空中”;萨拉“用一个银杯喝香槟酒”(4)。萨拉对热气球感兴趣是因为“我充满梦想的本性总是不停地将我带向更高的领域”(6),在她的短途飞行中,她坐在一把麦秸椅上,她关于乘坐热气球冒险的文字,也是“突发奇想地从椅子的视角叙述的”(6)。
导论1
第一章 变装表演——巴恩斯小说中的性别身份与性取向52
第一节 穿上女装的男人54
第二节 披上男装的女人83
第三节 性取向表演105
第二章 东方的他者化——巴恩斯小说的种族身份书写 124
第一节 作为外他者的东方人身份建构125
第二节 作为内他者的东方人身份建构153
第三章 英格兰性的想象——巴恩斯小说的民族身份认同 178
第一节 内部观照:解构乡村神话,突显中年
阶级意识 179
第二节 外部观照:突显英法差异,坚守英格兰民族个性204
结论233
参考文献244
后记(一)266
后记(二)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