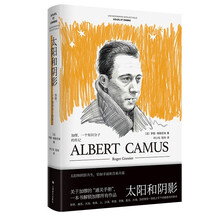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中国现当代作家图传:老舍传》:
老舍出身于晚清旗人家庭,1899年2月3日(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那天是送灶的日子)诞生在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羊圈胡同(现为小杨家胡同8号),取名庆春。父亲舒永寿,母亲马氏,庆春是小儿子,他大姐此时已经出嫁。舒家编属正红旗。
从历史来看,我们不可将旗人与满族人等同(旗人不仅包括满人,还包括加入旗籍的蒙古人、汉人等),辛亥革命以后没有了八旗军籍,旗人的等级身份消亡,满族的族裔身份依然合法存在,只是生活境况大不如前了。“旗人”和“民人”(即汉人,加入旗籍的汉人除外)是清朝人的两种迥异的身份,清帝国是八旗先人创立的国,民人身份普遍低于旗人,朝廷对待两种人的法律与衣食俸禄都不一样。进人民国时期,江山已经不再属于旗人,改称民国,低于旗人一等的民人有了名义上属于“民”的“民国”。民国初期的一二十年内,刚刚失去了政治经济特权的旗人生活极其艰难,虽然民人生活未必得到普遍改善,但比较起来,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心理方面都要比旗人好过一些。
老舍一出生就赶上了变法改良的年头,旗人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威胁,可谓生不逢时。改变“铁杆庄稼”的生活待遇的言论已经威胁着身在八旗的人们,《茶馆》第一幕的众多旗人,在变法刚刚过去的日子里,都有着惶惶然的感受。紧接着就是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老舍的父亲在与八国联军的巷战中阵亡。老舍出生于军人世家,但到他长大成人,已经没有朝廷的军事责任需要承担了。他晚年写作的《正红旗下》,既可作为自传,又可当做一个族裔与王朝的衰败史。童年的老舍是末代旗人,他的少年与青年阶段,是摆脱与超越清朝遗民身份、成长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记下了旗人遗民的形象和心路历程,同时他也不时地想着满族人对中国历史的贡献。
一、三岁失怙了解一个作家的生活语境,理解他的精神历程,而后才能把握他创造的那个文学世界,我们不能把老舍的生活和作品分割开来。那些源自老舍生活语境的图片历历再现了他的文学与文化世界。老舍的文学世界情感丰沛,但在作品中表现得很有节制。因为父亲在童年生活中的缺位,老舍在情感上与母亲的联系更为紧密:少了别人通常由父亲给予的精神支持,老舍更倾向于精神导师的寻找。母亲是最好的老师,童年、少年引导他向善的还有宗教界人士,青年时代他参与教会活动、服务社会。尽管幼年失去了父爱的“怙恃”,老舍却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保持着一颗爱心,日后把这颗爱心放大,体现在抗日战争中对“文协”工作的奉献,20世纪50年代对新时代的平民生活的肯定,更重要的是他一生对生活的巨大热情。
若是出于对老舍的崇敬,人们追思他的父母,却发现除去老舍写的《我的母亲》,其他关于他的父母的文字资料很匮乏,图片影像资料更是缺失严重。一百多年前西方来华的传教士的印刷品上就印有各种西方伟人的照片,上个世纪初上海滩上的红倌人的照片已经上了杂志,20世纪20年代洋太傅庄士敦身着御赐的貂皮褂在宫中照相,但是这项技术在中国为平民家庭所用却很晚。今天欲撰述上个世纪早期的生活,若非生于豪门且为知识界中人,身为平民而没有特殊因缘,则难以找到他们的照片。上世纪40年代,老舍在昆明西南联大,与一批知识分子共同度过了七八十天,仅仅留下了一张合影。吴晓铃先生曾感叹:“当时照相是真正高档奢侈活动。”1900年老舍的父亲死于与八国联军的交战中,当然不可能留下旗装卫戍的照片,连在民国生活了30年的老舍母亲也没有留下照片。也许老舍母亲做寿时拍过照而没能在战争中保存下来,老舍为老人祝寿唱大戏、放电影而不拍小照似乎不合情理,除非老太太有什么忌讳。对这个缺憾的弥补,就只能依赖于背景或相关材料,只好请读者将对文字的想象转变成画面了,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入侵的冲突、战争造成了老舍生活中父亲的缺位。老舍是老儿子,父亲舒永寿是护军,担当拱卫京师的职责。父亲和旗兵们在京城里与八国联军交战的时候,他才一岁半。1900年8月15日,正当壮年的舒永寿在战争中受伤致死,入殓的棺木中只有其生前穿的一双袜子和一副裤脚带。老舍对父亲肖像的记述源于父亲进入皇城的腰牌上的字迹:“面黄无须”。中年老舍自述:“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从他的中年照片可以想象得出其父舒永寿的容颜,也可以从正红旗护军译大典时所着礼服想见其当年的军仪。父子面容相似,而命运在六十多年后也水火无情的轮回:父亲死于战火,他则跳太平湖溺亡。父亲去世前后的年头,正是老舍《茶馆》《断魂枪》《神拳》这些作品中人事与生活的语境。在这些人事的叙述过程中,幽幽飘荡着老舍父亲的一丝气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