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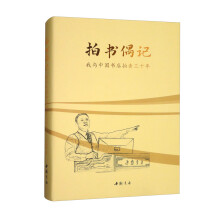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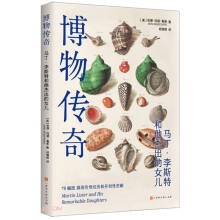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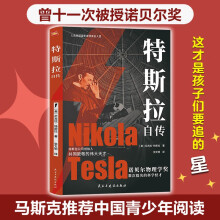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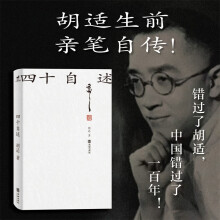
陈乐民先生1930年出生在北京,在天地玄黄的20世纪中国,他亲历了屈辱的日本占领,目睹了家族的衰弱,见证了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亲身参与了民间外交事业。改革开放之后,他又以半百之年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成为中国欧洲学研究的开创者。
作者在书中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所受的家庭教育,求学、工作和生活中经历的事件和人物,各时期人生理想的转变,主要学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参访域外的感想,深刻反映出一位优秀学人淡泊名利的精神风骨和融通中西的学术追求。本书不仅是一部作者个人的“私历史”,也是一部反映时代思想变迁的备忘录。
母亲是一旧式家庭的妇女,恪守礼教。她的性格是非常温和厚道的,在亲友中有很高的声誉,都很敬重她的为人。同时她又是非常重大义的,有两件涉及她本人和一家安危的事,是我一生不忘的。
一是在日伪统治末期,日伪警宪抓了许多壮丁,我家后院外有一处是关押“壮丁”的看守所,有日本兵把守巡逻。一次夜里,有些关押的“壮丁”哄逃了出来,从我家屋顶穿过,后面人声呐喊“抓人”,气氛十分恐怖。其中一个“壮丁”情急之间跳进我家院内,我家的狗随声狂吠;母亲立即叫我家厨师老夏把那个人藏进厨房。等事情平息下来以后,母亲给了那人一些钱和吃的,让他从大门逃走了。老夏事后说,大奶奶(指母亲)深明大义,我佩服。
再一次是内战晚期,北平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国民党军队时有逃兵,街头上时可见抓逃兵的告示。一天,一个国民党逃兵敲门乞食,母亲居然把他叫进堂屋给他饭吃,问他缘由,他说不愿再卖命当兵,要回家乡去,宁肯冒生命危险逃出军营。母亲怜悯他,给了他一些“袁大头”,嘱咐他一路小心。
这两件事,母亲都是冒了险的,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在十几岁时对我的旧礼教家庭已极有恶感,“宣布”家庭遗产,我一片瓦都不要。我以为会使母亲伤心,但母亲出我意外地赞许我这一点点“叛逆”精神,支持我;但以后又时常念叨“亏待”了我,因为我没有分得半点“遗产”。母亲在这个家庭中是我唯一敬重的人。
母亲没有留下任何遗物,我手头上保存的是唯一一张小一寸的黑白照片,母亲戴着老花镜在看书,那大概是她六十几岁的时候,当时早已搬离已经“交公”的旧居了。她样子十分平和,好像不曾经历过生活磨炼似的。
在过去,老百姓最厌恶、痛恨和害怕的,是那些狐假虎威的“保甲长”,他们是直接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只要他们找上门来,就一定是降下了灾星。老舍写的《四世同堂》,一点都不差。有一回使我们全家都“动员”起来了。几个日伪“保甲长”之类的爪牙来了,喊叫着说上面的命令要查“禁书”,凡是存有讲国民革命、三民主义、颂扬国民党等内容的书都要严查,严重的要坐大牢。那时,凡是读书人家,谁能没有这类书籍呢。后来,不知怎的,母亲取得“爪牙”们的“宽限”:承诺在几天之内使有关违碍的字句“销声匿迹”。“爪牙”们离开后,母亲率领全家凡识字的人,把有关这类内容的书勘查一遍,有的整本毁掉,有的发现其中有这类字句,即用墨笔涂掉,而不管上下文如何。反正他们再来时找不到这类字句就是了。折腾了一阵,“爪牙”们又来了,说“可以了”,扬长而去。母亲是不是给了他们一些“好处”,我年幼,不得而知。
题记
从“家门”到“学校门”
一个“大家庭”的衰落和我的少年启蒙
我走马灯似的上了四所大学
马不停蹄,岁月流逝
进入“机关”门
维也纳——我生活四年的欧洲城市
从回国到“文化大革命”
看的是欧洲,想的是中国
人生行旅中的“中转站”
什么叫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
从对国际问题研究的若干思考到康德的魅力
两种文明-全球化-世界历史
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岁……
域外拾遗
我记忆中的人文法兰西
德意志民族情结——分裂与统一
奥地利访旧
浮光掠影意大利
“虚君”与宪制民主的不列颠
印象模糊的亚非拉
物化加政治的美利坚
后记
我这一生分三段:大学毕业以前读书;青年和中年是从事“民间外交”的“小公务员”;进人老年则乔列为“学者”,主要关注欧洲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这个范围内的问题。用两句话来说,就是:“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我想,我之所经历,我之所思所想,也许对于青年人了解所谓“另一代人”的生活环境、思想和精神状态,有些许用处吧。
——陈乐民
1948年高中毕业、1953年大学毕业的陈乐民先生当属“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代和“新知识分子”的第一代。在这“一身跨两代”的特殊一代人身上,无论是新旧矛盾、冲突还是新旧调适、传承,表现都非常“典型”。可以说他们是破旧立新的一代,也可说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因此,“阅读陈乐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
——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