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即人性
那么,谁才是现实主义者呢?我认为现实主义者是上述那些将文化作为人之存在的原始状况,而生物性只是次要的和条件性的人。从批判的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对的,而且人类进化的古生物学证据也能支持他们,格尔兹也出色地给出了人类学上的暗示。文化要比原始智人早上许多时代,并且文化是人类生物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链条中的文化证据可以追溯到距今300万年前,而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不过几十万年之久。著名的人类生物学家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Klein)认为,根据解剖学上的证据,现代人类仅存有50,000年之久,尤其是在石器时代晚期才兴盛(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使得文化的历史是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的六倍。(但是克莱恩为了强调旧石器时代晚期基于生物的文化进步,而有意系统地贬低早期人类灵长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成就。)更重要之处在于,在这300万年中,生物是在文化选择下进化的。我们为了文化的存在而形塑了我们的身体和精神。
顺便插一句。谈到身体和灵魂,我们应该注意到西方传统中的前辈们,曾提出有关身体和灵魂进化的平行概念。当柏拉图宣称精神是唯一能自我运动的实体,且早于它所推动和形塑的身体时,他也许有意贬损了某些智术师。进一步说,因为精神是在艺术、法律及其类似中实现的,这也就是说nomos早于physis,并且是它的源泉。他在《法律篇》《蒂迈欧篇》《斐多篇》和别处中都有这样的看法。在《法律篇》(10.896a-b)中他说,身体是次要的衍生物,并从属于精神,这意味着“意识、意愿、深思熟虑、真的判断、目的和记忆等的心绪与习惯,都要先于物理的长、宽、深”。那就是说,文化先于自然:
意见、勤勉、理性、艺术和法律总是先于粗糙和光滑,重和轻。特别是那些巨大而原始的作品和造物,正是因为它们属于“原始的”范畴,所以属于艺术。自然的东西和自然本身——使用我们对手的错误术语——是从艺术和理性派生出来的第二性产物。(10.892b)
我们为什么这样错误地称呼自然呢?因为精神/文化是第一性的,精神才是最好的自然性(《法律篇》,892b-c)。或者用当代人类学的话说:文化即人性。
言归正传。怀特(LeslieWhite)常说,猿不能区分圣水和蒸馏水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两者在化学上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它们意义上的不同导致了所有的不同:人们如何评价和使用圣水;与猿不同的是,无论它们是否口渴,在这方面都不会有不同。这是我关于“象征”是什么和“文化”是什么的简要介绍。就人性的意义而言,依据文化而生活,就意味着不但有能力以象征的方式成就我们身体的习性,也承认以象征方式成就我们身体之习性的必要性,即是说,依照我们充满意义的决心和存在对象而生活。这种对身体、身体需求以及动力的象征性笼括,是长期文化选择的重要后果,正是从此当中产生了智人。
现在很多生物学的观点认为,人的大脑是一种社会器官。它是在更新世维持相对复杂而团结的社会关系的压力下进化的;这社会关系甚至可能包括和非人类的关系。象征性的能力是这种社会能力的必要条件。这种“压力”将使人变成文化性的动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将我们的动物性文化化了。我们并不是,曾经也不是一块“白板”,缺乏任何生物性的需求;相反,正是这些需求和多种多样的意义才选择构成了原始人这个独一无二的“种”,因此是以隐秘的方式实现这些需求的能力,而这正是考古学、历史学和民族学已经证明的事实。我也并不是反对现在流行的共同进化论:文化和生物的发展互惠性地相互促进。但这并不表示它们在人类的社会性存在中占据同等的价值。相反,在多样和复杂的文化类型与特殊的生物习性之间必须是悖反的关系。共同进化论认为,文化的发展必须得益于驱除生物性冲动或者惯称的本能行为。其结果就是生物性功能被组织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中,以至于生物性需求的表达取决于有意义的逻辑。正如格尔兹所说,我们原本可以尝试数以千计的生活方式,但最终我们只按照一种方式来生活。只有当生物性的需求和驱动并不能确认实现它们的特殊方式时,格尔兹所说的才成为可能。生物学成了被决定的决定性因素。
所以再问一次,谁才是现实主义者?难道不是那些斐济人嘛?他们认为孩子们具有“水之灵”,这意味着在掌握斐济习俗之前,他们都不是完整的人。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群持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人性是基于领会和实现某种文化图示的能力,它是“正在形成中”的(abecoming),而不是天生已经存在的。正如伯克(KennethBock)指出的,我们关于人性神话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将人性错误地推定为是一个实体(entity)。我们谈到在某种程度上犹如嵌入在种质中的决定性的文化实践:最切近的是在基因中,此前则是在本能中,再前则是在精液中。所以,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人性是这还是那,是好还是坏,问题在于生物学主义本身。人们已经对蒙田、霍布斯和曼德维尔学派提出了很多批判,他们在抨击天生的利己主义时都基于人性天然的善或天然的社会性,可是,这仍然没有逃脱类似的文化形式的肉体决定论框架。正如伯克也指出的,真正的另类看法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潮,这思潮将人性从原罪的命定之恶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方面,伯克挑选出皮克·德拉·米兰多拉(PicodellaMirandola)的《论人的尊严》(OrationontheDignityofMan)这篇文艺复兴时期关于自我形成的经典文章。这篇文章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想创造一种懂得欣赏其美丽和伟大的造物;但是当他由此开始制造人类的时候,却并没有形式或空间可以做这一项工作。皮克写道:所以,既然上帝不能赋予人类完全是他自身的任何东西,于是上帝决定将人变成一种“没有确定形象的造物”,并且将他置于世界的中心,这样可以让人类分享别种造物的天赋。上帝对亚当说:
其他造物的本质一旦被规定,就都为我们定的法则所约束。但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你的自由意志决定你的本质,我们已把你交给你的自然本性。……我们使你既不属于天堂也不属于俗世,既非可朽也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自己尊贵而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你能堕落为更低等的野兽,也能照你灵魂的决断,在神圣的更高等级中重生。
除了人类固有的能够拥有的上千种生活方式之外,我们也想起露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写到的充满许多可能性的大圆弧,每种文化都是在这个大圆弧上的选择性开发,但都只是它的一个有限截面。
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家们,尤其是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on),执起人类意志的事业,反抗宿命的原罪或本能时,他们增加了一个社会的维度,从而导向了人类学式的理解,把人性理解为文化形塑的形成过程。弗格森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原罪,则道德中介是无意义的,因此,他的说法超出了一般的对于自由意志的辩护。对弗格森来说,人实则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但他的天性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而不是先在地已经形成或者为这种先在负责的某种东西。没有所谓前社会的个体,也没有存在于社会之前或者之外的人类。人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无论好坏,且在不同的社会中人都是多样性地形成的。弗格森(在孟德斯鸠之后)说道:他们生于社会并于此能掌握所有的情感,不同的人群在这些情感的基础上塑造他们自身的生活模式。弗格森从人性必要的社会构造中总结出,“如果我们因此要问,哪里才能找到自然的王国?我们可以回答说,就在这里——无论我们所说是在大不列颠岛、好望角还是麦哲伦海峡,都没有关系”。
同样,马克思也认为人的本质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人的本质是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而不是一些蹲在宇宙之外的可怜家伙。如果是在欧洲的背景下,按照自我中心主义的方式,人只有在社会的情境中才能将自己变成个体——正是这个形象促使经济学家假定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成年男性的性情,并由此建构出他们自身科学的幻想(鲁滨逊式的人)。马克思并没有从天性角度来谈社会的形塑过程,尽管我们完全可以从相反的方向来看这个问题:从资产阶级社会到神话般的一个人对抗全体人的霍布斯式战争。人类生而非善非恶,而是在社会行动中塑造他们自身,如同在既定的历史画卷中展开那般。也许有人会认为,马克思关于殖民化他者的知识促成了这种人类学。无论如何,在马克思那里,他用“既定的文化秩序”替代了“既定的历史状况”,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换句话说,人们用以塑造自身的实践(praxis)是通过文化形成的,这种对人之生存条件的理解已经成了民族志的常识。
自然状态“就在这里”,因为文化就是人的本性。当爪哇人说“成为人就是成为爪哇人”,记录这一点的格尔兹认为他们是对的,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如人性,不是依赖于文化”。玛格丽特·米德在《在新几内亚成长》(GrowingupinNewGuinea)中回应了卢梭关于教育者们的观点——教育者们要清除思想不正的成年人加在孩子身上的扭曲的人性,“但是,更妥当的态度是把人性看作是最粗糙的、最没有差别的原材料,如果它不受文化传统的形塑,将没有任何值得确认的形式”。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人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中形成了自身,但是问题依然在于,是传统给予了他们肉体需求和满足的模式。
我们以性为例子,最关乎生物学和文化之关系的问题在于,不是所有文化都有性,而是所有的性都有文化的内涵。根据地方文化所认定的合适的伴侣、场合、时间、地点及身体实践,性欲望有不同的表现和抑制方式。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升华一般的性,包括它的超越形式——赋予独身更高的价值,这也证明了在象征的领域,达到不朽有更多的强制方式,而不只是含混神秘的“自私基因”。毕竟,不朽是一种彻底的象征现象,不然还能是什么呢?(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满足于在想象中预期死亡可能带给他们的名望,总是自愿地追求死后的名望,但他们已不能再享受那名望。)同样,性也是通过多种意义秩序的形式来实现的。想想甚至有些西方人在电话里做爱,更不用说有人认为打猎是做爱的奇妙方式。或者再举一个玩弄概念的例子(双关),比如比尔·克林顿说:“我和那个女人没有性关系。”
不仅是性,其他内在的需求、冲动或性情,比如滋润的、好斗的、友善的、怜悯的,不管它们是什么,都取决于象征性定义,因而也是取决于文化秩序。进攻性或支配性也许会采取行为的形式,如《纽约客》回应“祝您今天过得愉快”时说:“不要命令我如何做!”我们都在伊顿的游戏场里战斗,相互诅咒和羞辱,用不能互惠的礼物实施支配,或者给学术上的敌人写攻击性的书评。爱斯基摩人说礼物造就奴隶,如同口哨役使狗群一样。但是想一想,或者想想我们自己相反的谚语:礼物带来朋友——这种说法如同爱斯基摩人的说法一样,也针对着流行经济学的成果——这意味着我们也是生而具有“水之灵”的,等着历经某种有意义的独特生活方式时,才彰显我们的人性,不管是好是坏。但是,绝不像在古典哲学以及现代科学中那样,我们由于遭受到无可抗拒的人性的诅咒,只能靠牺牲相关他人来成就自己的利益,并由此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社会存在。
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我谨慎的结论是,西方文明建立在一个对于人性的顽固而错误的看法之上。对不起,请原谅;这不过是一个错误而已。但这种对人性的错误观点危及我们的存在,这倒可能是真的。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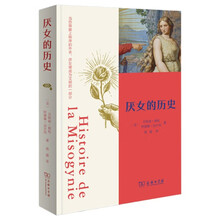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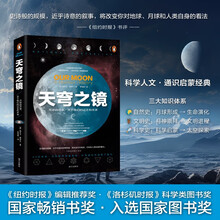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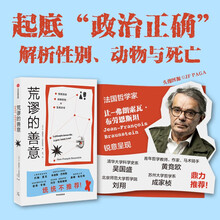





在此收录的三篇着述……不仅仍旧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它们编辑成册,以其中一篇文章的题目《人性的西方幻象》为书名重刊。希望这本小册子有助于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现实世界及其吊诡的理解与反思。
——王铭铭
当亚洲于18世纪进入欧洲的意识当中时,它马上就被当成了治疗剂。作为香料和毒品、美食与养生之地,东方,一如德米尼所言,不仅以其绚烂的外表让欧洲目眩神迷,也是潜入整个欧洲躯体的一种存在。
——《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宇宙观》
身体必须以特别强烈且非常痛苦的方式承载社会结构。……在西方历史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人们对一切人类社会和人类行为的看法,都一度通过个人快乐和痛苦的美妙转喻而在常识和哲学层面上得以表达考察。
——《甜蜜的悲哀》
西方文明建立在一个对于人性的顽固而错误的看法之上。对不起,请原谅;这不过是一个错误而已。但这种对人性的错误观点危及我们的存在,这倒可能是真的。
——《人性的西方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