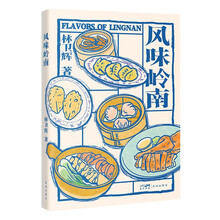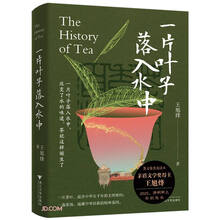素烧烤麸
上海人的童年记忆离不开烤麸的味道,绵糯烤麸里包着的不仅仅是满满的微甜汤汁,更是萦绕着浓油赤酱的上海滩旧时光的滋味。但每次在北方大谈烤麸的美味时,十个听众里面总有八九个露出狐疑神色——那是什么?此时,只需将“烤麸”二字替换成“面筋”,便往往能收获无数恍然大悟的认同感,绝无甜咸豆腐脑争斗之虞。
烤麸与面筋,名字上看着毫无关系,实际上却并无多大区别,都是将面团反复搓洗后或蒸或烤或煮,出现的一份份蜂巢般充满孔洞的柔韧产物。那一个个细小的空隙,便是日后用来吸收香浓汤汁的美味所在。
正是由于擅长吸汁入味,烤麸此物,在实用百搭这一方面,简直能与豆腐比肩。其吸满汤汁、满口留香的质地,也与冻豆腐相差无几,只是口感上更为柔韧耐嚼,多了几分风骨。
也是因为这一份毫无性格的百搭特性,南甜、北咸、东鲜、西辣,不管你宴请的是来自大江南北的哪一位客人,都能从一盘做法不同的烤麸或面筋中找到满满的归属感。
传说烤麸源自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这位皇帝生性节俭、笃信佛教,不但长期茹素,还曾经亲自跑去寺庙出家,更下令将祭祀神灵的牛羊牺牲改为用面捏成的牛羊模型。烤麸由信佛的梁武帝发明虽然并无史料证据,但后世的僧院名刹,倒是真的多半擅长料理面筋或烤麸——形形色色的素鸡、素肉、素鱼,不少就是由朴素的烤麸加上花样百出的汤汁烹饪而来。
爱吃烤麸的僧人实在太多,其中最有名的,恐怕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僧释仲殊。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里回忆仲殊,说他爱吃面筋,但吃法异于常人,喜欢“渍蜜食之”。“渍”也就是腌渍的意思,“渍蜜”多半就是用蜂蜜腌渍面筋后吃。这样的做法不但我们现代人看着像“黑暗料理”,宋朝人也纷纷表示难以接受,以致“客多不能下箸”。唯独苏东坡与他一样嗜甜如命,将蜜渍烤麸吃得津津有味——怪不得二人能成为至交好友,谈诗作赋的文艺情怀,恐怕还没有一碗蜜渍烤麸的友情来得浓郁绵长。
钟爱烤麸的古人远不止仲殊与苏东坡,南宋的吴自牧在《梦粱录》里怀念故都临安过眼云烟般的繁华盛况时,就一口气写了若干种烤麸的吃法,如“鼎煮羊麸、乳水龙麸、五味熬麸、糟酱烧麸、麸笋素羹饭、麸笋丝假肉馒头、笋丝麸儿”等,足见当时的南宋人民已与当代的我们口味相仿,烤麸多半爱以红烧,并搭配清新素雅的笋丝或浓墨重彩的糟酱,各具风味。既是情之所钟,难免要为烤麸作诗写情,诗人王炎说它“色泽似乳酪,味胜鸡豚佳。一经细品嚼,清芳甘齿颊。”宋无亦则写得更为直白,“山笋麸筋味何深,箸下宜素又宜荤。黄润光亮喜入眼,浓汁共炙和鸡豚。”不是吃了无数碗浓汁烧就的肉焖烤麸,想必是写不出“黄润光亮喜入眼”这般直抒胸臆的句子吧。
清代大美食家袁枚同样极爱烤麸,并且倾情提供了几个方子,“一法,筋入油锅炙枯,再用鸡汤、蘑菇清煨;一法,不炙,用水泡,切条入浓鸡汁炒之,加冬笋、天花。上盘时宜毛撕,不宜光切。加虾米泡汁,甜酱炒之,甚佳。”一口气包揽了油面筋、水面筋、红烧、清炒等多种做法,还念念不忘地叮嘱了细节——不要把烤麸切得过于规整,用手来撕,更有随兴为之的美感。
烤麸宜荤宜素,宋无亦与袁枚想必更喜荤烧,却也有不少人偏爱素食。《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化缘的食钵里常见素烧烤麸,而八戒吊在金角、银角二位大王家的房梁上,心心念念的除了饱肚子的精米细面,也就是“竹笋茶芽、香蕈蘑菇、豆腐面筋”了。《红楼梦》里的晴雯姑娘,也曾特意差遣小丫头小燕去厨房里嘱咐要一碗芦蒿炒面筋,还要“少搁油才好”。为此,厨娘柳嫂子还调侃大观园里的姑娘们,每日细米白饭肥鸡大鸭子吃腻了,这才闹起面筋豆腐酱萝卜的故事来。
现代社会不同古时,普通人也如贾府里的少爷小姐一般,每日里细米白饭肥鸡大鸭子吃得腻歪了,家宴上若能出现一碗素而不淡、柔韧多汁的素烧烤麸,想必更能吸引大家的筷箸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