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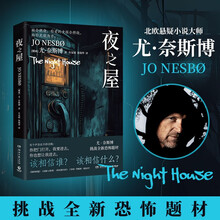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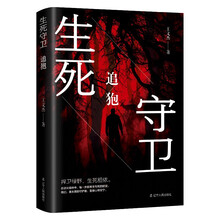




比尔斯被誉为美国百年文坛怪杰,可与爱伦•坡比肩,更对海明威影响深远。他一生富有传奇性,成名之后却又神秘消失,不知所终。其生平被拍成电影,与他的小说一样,被喜欢恐怖小说的读者追随。比尔斯的作品以离奇怪诞的题材闻名,敢于挑战人性中隐秘的弱点和阴影,讽刺辛辣,一针见血,可谓后世西方一切黑色幽默的开山鼻祖。《海上梦魇》将现实主义与超自然元素相融合,一流的悬疑,极致的惊悚,惊险的故事,给读者带来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
这是一个奇冷无比的夜晚。天气晴朗,空中清澈得就像一块钻石的中心。晴朗的天空往往寒意更浓。虽说在黑夜,就是冷也未必觉得,可当你能悟出冷时就觉得受不了。这晚的天空异常清澈,因此气候也就显得更冷了,仿佛一个人挨了蛇咬,简直痛入骨髓。月亮在南山顶高大的松树后面神秘地挪动。已经冻硬了的雪地上,辉映着清冷的白光。西方黑乎乎的天幕下,隐隐现出鬼魅般的海岸山脉轮廓。山脉那边是太平洋。雪沿着峡谷底部开阔地伸展,有的堆成长长的山脊,高低起伏;有的堆成小丘,像是四处飞溅的浪花,那浪花其实是月亮投射到雪面之后辉映出来的白光。
矿山营房的废墟中,许多破旧的小屋都被雪湮没了(水手们会说它们沉没了)。偶尔,连那曾经架起水渠的高大的栈桥也都盖满了雪。栈桥上是一条叫做作“弗鲁姆”的水渠。“弗鲁姆”就是拉丁语“弗鲁门”的同义语。生活在大山中的淘金者自有其生活的优越感,其中大山不能从他们身上剥夺的就是他们说拉丁语的权利。人们谈起死了的邻居时说“他到渠上去了”,比说“他命归黄泉”更委婉一些。
大雪穿上铠甲抵御寒风肆虐的同时紧紧抓住每一处有利地势。它像是被风驱赶的俨然撤退的大军,在开阔的地方摆开阵势:能立足的地方立足,能藏身的地方藏身。偶尔也能看见整片整片的白雪躲在断壁残垣之后。山腰上凿出的那条崎岖的废弃山路也堆满了白雪,那白雪一队接着一队地争先恐后从这条道上逃去。冬天的子夜里,人们再也想不出比“死人谷”更凄凉、更阴森的地方了。可是希拉姆·比森偏选中这里,成为这里唯一的居民。
他的松木小屋就在北山的山腰上。一束微光穿透小屋仅有的一块玻璃,整个小屋看上去宛若一个用崭新发亮的别针别在山腰上的甲壳虫。屋内,比森先生独自坐在熊熊的炉火前。他出神地盯着红通通的炉内,好像平生从没见过那种东西似的。他长得并不好看,头发灰白,衣衫褴褛,不修边幅,脸色苍白憔悴,两眼炯炯发光。至于他的年龄,人们可能先是猜四十七岁,随即纠正说七十四岁,而实际上他才二十八岁。他形容枯槁,也许马上就能见本特利洼地那位拮据的殡葬员以及索诺拉那位满腔热情的新任验尸官了。贫困和热情就像上下两块磨石,在这种三明治中充当夹心真是危险。
比森先生坐在那里,双肘撑在膝盖上。肘关节和膝关节处的衣服都已破烂不堪,干瘦的双手捧着干瘪的下巴。他还没打算上床。此时,他看起来好像只要稍微挪动便会绊倒,摔得粉身碎骨。尽管如此,在过去的一小时里,他的眼睛还是眨了不止三次。
突然,屋外响起了刺耳的敲门声。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天气里的敲门声,对一个在峡谷中住了两年都没见过一张人脸,又很清楚这一地区道路不通的人来说,准会大吃一惊。然而,比森先生只是抬眼看了看,甚至在门推开时,他也不过耸了耸肩,缩了缩身子而已,犹如人们在等待什么东西却又不愿看到,又好像殡仪馆里的妇人,等着棺材从身后走道上抬来时才露出无奈的样子。
走进门来的是一个瘦高的老头。他身穿绒毛外衣,头上裹着面巾,脸上蒙着面罩,眼珠发绿,露在外面的脸煞白煞白的。他进来时,迈着阔步,却没有一丝响声。老头将自己戴着手套的僵硬的手放在比森先生的肩上,比森先生不由自主地仰起头,脸上失去了血色。不管他在等谁,很显然,他没料到自己迎来的会是这样的人。然而,见到这位不速之客,比森先生百感交集:惊诧,感激,最后是深深的祝福。他站起身,从肩上抓起那只青筋突出的手,热情地和老头握了两下。那股热情真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就老头的外表而言,一点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没有,有的倒是令人厌恶。然而相对厌恶,魅力总是无处不在;而厌恶尽管无处不在,但不为人重视。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东西要算我们在脸上本能地蒙上遮羞布,若想再注目一点或者更迷人一点,就再在上面堆上七英尺厚的泥土。
“先生好,”比森先生说着,松开了老头的手。那手自然垂下,轻轻地落在他的腿上。“天气太糟糕了,请坐,见到您真高兴。”
人们怎么也难以想到比森的话竟会那么随和,那么文雅。真的,他的外表和言行反差太大了,谁也不相信这会是矿上最为普通的一种交际现象。老头朝炉火前走上一步,深陷的绿眼珠闪着亮光。比森先生接着说:“我真的很高兴!”
其实,比森先生的话还不算十分文雅。那话早已降低了标准,带有当地的味道了。他停了片刻,目光从来客的面罩向下,掠过那排发霉的紧扣着的大衣纽扣,最后落在那双发绿的牛皮鞋上。鞋上沾着的雪泥已开始融化,一股股地流到地上。他审视完自己的来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谁都会满意的。然后,他接着说:“真不巧,我只能照现有的一切来招待你了。不过,你若不嫌委屈,愿意跟我在一起,而不想到本特利洼地寻找更好的住处的话,我感到十分荣幸。”
比森先生的话既殷勤好客,又谦卑讲究,好像在说老头在这样的冰天雪地走上十四英里,来到他的温暖小屋,简直是种无法忍受的痛苦。作为回应,老头解开外套。主人在火上又加了块煤,用一只狼尾巴掸着炉床,接着道:“但是我又想,你最好快点离开这里。”
老头在炉边坐了下来,把那双宽大的鞋底伸向炉火,没有摘下帽子。在矿上,人们很少脱帽,除非脱掉鞋子。比森先生没有再说话,也在一个椅子上坐下。这椅子原来是一只桶,还保留着它原来的特征,好像是为了收藏他的骨灰而设计的,倘若能使他粉身碎骨的话。霎时间,小屋又沉静下来。这时,远处松林里传来一只恶狼的嚎叫声,门框嘎嘎作响。两者的相连意味着狼厌恶风暴,而风却越刮越紧了。然而两者之间似乎又有一种诡谲的巧合。比森先生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打了个寒颤。他很快又定了定神,再次对他的客人说道:“今晚这儿有些蹊跷,我将一切都告诉你吧。当然,如果你决定要走,我可以送你走过那段最可怕的路,一直送到鲍迪·彼得森枪杀本·哈克的地方。我想你知道那个地方。”
老头用力地点了点头,像是暗示他不仅知道,而且非常熟悉那个地方。
“两年前,”比森先生开始说道,“我,还有两位同伴,住进了这间房子。在人们都涌向洼地时,我和其他人也一道离开这里。不到十小时,整个峡谷里的人都走光了。可是那天晚上,我发现自己落下了一只珍贵的手枪(就是那只),便赶回来取。结果我独自一人在这里过了一夜,从此每夜都在这里度过。我得说明一下,就在我们还没离开这里的前几天,我们的中国佣人死了。那时天寒地冻,很难像平常那样给他挖个坟墓。于是我们匆匆离去的那天,只好把地板挖开,草草地安葬了他,但人还没入土。我十分没趣地剪去他的辫子,把它钉在坟上的横梁上。那地方你这会儿就能看见,不过最好等你暖和了再慢慢看。我有没有说那个中国人是老死的?当然不管他怎么死,都与我无关。我回来,既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无法抵制的诱惑,也不是鬼迷心窍,只是因为我把手枪忘在这里。这你很清楚,对吗,先生?”
老头神情严肃地点了头。他看上去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即使有话,也不多。
比森先生继续道:“根据中国人的信仰,人就像风筝,没了辫子尾巴就上不了天。哎,长话短说吧——可是我认为还是说一下好——那晚我独自一个人在这儿,怎么也没想到那个中国人回来要他的辫子。他没有拿到。”
说到这里比森先生再度陷入沉默,茫然若失。也许因为他不太习惯说那么多话,也许他突然想起什么,不能分神。这时风声四起,山坡上的松树被风刮得格格作响,声音异常清晰。
鬼屋之夜
古宅惊魂
邪恶的鬼魂
诊断死亡
卡可索的永恒魂灵
闹鬼的山谷
犬魂
行尸游荡
鬼谷谜云
恐怖的葬礼
盗尸者
孪生兄弟
幽灵返乡
转世灵魂
林中活尸
复仇冤魂
不速鬼客
幽灵情思
鬼魅世界
海上梦魇
猫头鹰桥上的恐怖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