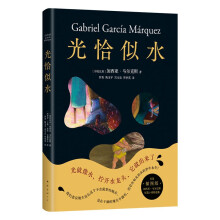杏的眼
李佩甫
一
在我们傅夏祁,有一棵老杏树。
这棵老杏树很有一些年头了,没有人知道它的树龄和历史。它不是一般的杏树,它的名字叫“十里香”。
在我们童年的记忆里,这是一棵会飞的树。有时候,在我们的梦中,它像云霞一样,在天上飞。
童年里,我们曾结伙偷杏。在我们结伙偷杏的小伙伴中……有一个人,后来成了我们的骄傲。
他的名字叫祁小元。
二
最初,没人把祁小元当作恩人。
那时候,他刚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穿一身绿军装,走路直杠杠的,甩着两只手,好像胳膊不会打弯儿似的。关键是他不会蹲了。当我们蹲在地上的时候,他仍然像旗杆一样立着。一米七八的个头儿,使人不得不仰望他。自然,本地话也不会说了,撇一口京腔。有一段,私下里人们都叫他“狗啃麦苗”。
“狗啃麦苗”也就罢了。当了几年兵,他竟然还吹嘘说他曾在天安门站过岗。人问他:啥门?他说:天安门。这就有些大了。是不是?天安门能是你站的地方么?!吹吧。
祁小元也不解释。扭过身去,直直地就走了。很骄傲的样子,这一点尤其让村人看不惯。
当然,祁小元是当兵回来后,才让人看不起的。后来,通过邻村跟他一块当兵的战友,他的底细慢慢就让人套出来了。是的,他的确在北京当过四年兵,也就是站岗放哨,没干过别的。据说,在北京当兵那四年,他专门买了一个小收音机,每天揣在裤兜里,以听新闻的名义,悄悄地练习说普通话。比如:你好。同志们好。红粉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红粉墙,红凤凰、粉凤凰之类,他想干什么呢?没人知道。据说,为了练好这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早上四点起床,站在故宫的院子里,大声念“啊呀呜、勃波莫否……”喉咙喊哑了,“啊”一嘴的血沫子。练到最后,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北京人。有人问他:你哪里人?他说:傅夏祁。人问:哪个旗?他仍然说:傅夏祁。北京人不敢再问了,怕自己没学问,到了也不知道他属于什么“旗”?
还据说,当兵期间,他是很努力的。原本想留在北京,如果能提干的话,最好找一个北京姑娘。在北京当兵四年,他给排长洗了四年臭袜子。可最后也只是当了三个月的代理副排长,而后就复员了。这都是传闻。
所以,他刚刚复员回来的时候,就有了这样一个绰号,叫:“狗啃麦苗”。
不过,一年零九个月后,就不一样了。
三
那时候,十里已是很远。
“十里香”就栽在夏家的院门外,它曾是全村人的饭场。
春天里,每当杏树开花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动了。我们结伙趴在场院的麦秸垛上,望着远处烟霞一样的杏花,齐声高喊:夏保兰,夏保兰,同桌祁小元!
不久,夏家院子里就会传出一声夏家奶奶的骂声:滚!
是呀,我们是看杏花的。那遒劲老枝上开出的杏花,娇艳粉嫩,花瓣一霞一一霞在阳光下亮着。在有风的日子里,花瓣飞起来,一瓣瓣在空中旋着,像雪、像船、像梦,粉色的。
它离我们很近。
它离我们很远。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