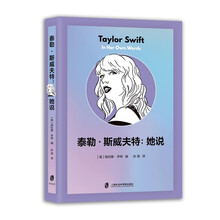就是这样想着的时候,爱玲的耳朵也还一直在倾听着门外的另一些声音,大门的每一次开关,巡警咕吱咕吱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睡里梦里都是这种声音。还有通向大门的那条煤屑路,在人的脚下发出沙沙的声音……越是艰难无助,求生的欲望越是一日比一日强烈起来。
父亲终究还是下楼来了,瞒过妻子孙用蕃,来到女儿床前,给她打了一些消炎针。不管这位父亲此举的目的是什么,不论是怕这个叛逆的女儿因他而死坏了张家的名声,还是做父亲的于女儿的最后的那一丝不忍,他的那一举动,给爱玲带来了转机。
爱玲的身体慢慢恢复,能下地慢慢扶着墙走路。这时,离爱玲被关起来的那一天,已经过了半年。半年时间,就在那间空阔冰冷的大房子里,囚禁自己的不是歹徒恶霸,而是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父亲。父亲虽没有置自己的女儿于死地,却将女儿的一颗心打进万劫不复的地狱。爱玲对家、对父亲的最后一丝留恋终在那漫长无际的囚禁光阴中一点点耗尽了。她只想离开。
她向何干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弟弟子静也悄悄给她送来了望远镜。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待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母亲知道,爱玲那一走,就算是与她身后那个强大的经济后盾彻底脱离关系了,她让何干捎口信给爱玲:“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当时人虽然被禁锢着,渴望自由的愿望压倒一切,但母亲抛出来的问题还是让爱玲痛苦犹豫了良久。后来,她还是想通了,那个家里,虽然满眼的钱进钱出,可那些钱不是她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到她。那样一想,她立马就决定了。
隆冬的晚上,她伏在窗子上,举着望远镜看看远处的黑路上没有人,拉开门,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去门闩,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了。没有人发现,没有人追上来。寂静的人行道上,连风也没有。一九三八年初春,上海街头,似乎只剩下寒冷了。暗沉沉的街灯底下,一片寒灰。爱玲的眼里,那一片寒灰的世界,竟是那般可爱可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重获自由的感觉实在是好哇。爱玲沿街疾疾向前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她遇上一位黄包车夫,她要坐他的车去母亲家里。许是心情大好,让她暂时把自己身后的危险弃之不顾,竟然与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