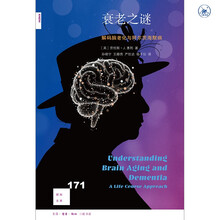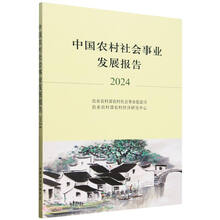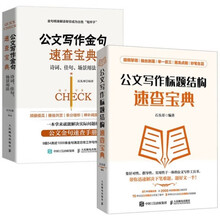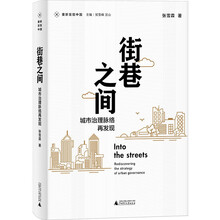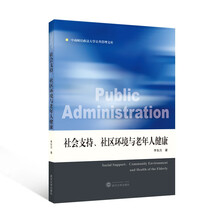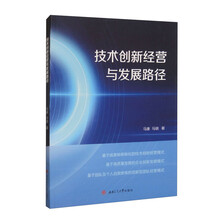《知识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学家: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
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的创始人,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他的小说以喜闻乐见的大众风格见长。在对民间文化的无限亲和中,赵树理走着与鲁迅等“五四”作家迥然不同的“启蒙”之路。然而,赵树理创作由鼎盛走向衰退,以及由特殊的意识形态原因导致的命运悲剧同样凸显着文学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身份认同的复杂性。赵树理曾给了自己三种身份认定:农民、革命者、知识分子。但这三种身份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赵树理出生并成长于山西一个极其贫困的农民家庭,从有记忆开始,家里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他有着和那个年代中国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经历,能体验到贫苦农民的切肤之痛。父亲是乡村说书艺人,因此,山西地域文化的熏陶、浸染、潜移默化形成了他固执而难以更改的乡土习性。而对于作家来讲,似乎痛苦和磨难比一帆风顺更有价值。抗战时期,青年赵树理曾经有过流离失所的避难经历,更使他有了普通老百姓朝不保夕的生活体验:赵树理的父亲、一个本家叔父,还有故乡村庄30多个善良无辜的农民,被“清乡”的日本鬼子用刺刀活活刺死,尸体被焚烧。加之他漂泊期间在“任何一个饭桌面前都难以站稳一年脚跟”的具体生存窘境,我们不难理解他为何要那么深情地为农民写作。这是促成他“农民身份”认定的基本因素。人生意识是由许多偶然事件和契机的触发而渐渐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当然,人生意识确立以后,偶然事件也沿着某种固定的仿佛是预设好的方向发生演变。这是因为人生意识一经确立,就强有力地支撑着个人的心理格局,从而同化、整合着那些干扰侵入的外界刺激。赵树理底层生活的偶然和不幸,促成了他为农民写作的人生及创作意识;这种写作立场形成他个人写作的稳定的心理格局,指导着他整个的写作生涯,亦确定了他对农民身份的认同。
在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求学的赵树理,开始也是抱着混饭吃的愿望,希望通过读书谋一个小学教员的饭碗。但在远离乡村生活的新环境和新生活群体中,赵树理自认为天经地义的乡土价值观受到严重的冲击,在“五四”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挑战”下,赵树理逐渐转向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认同。他这个时期创作的两部小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赵树理自我身份确认的转移。1934年,赵树理发表了小说《到任的第一天》,流露出出身乡土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留恋与羡慕,在想“把自己打人农民的生活里”的遐思中,已不自觉地把自己划在了农民阶层之外。1935年发表诗歌《耳畔》,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虽然作者极想和“锄地挑粪的角色”“同锄同挑”,但这个运用“他们”的称谓,则把自己划出了农民阶层。
虽然在自我身份的确认中,赵树理无论在主体认识还是小说创作都不无自觉地将自己划入知识分子行列,但由于其出身和早期知识结构中的民间文化因素,使其在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选择上不可能离开民间而走向庙堂和广场。接受了“五四”精英文化熏陶的赵树理兴高采烈地回家实践“启蒙”,却被自己的老爹泼了一身的冷水:被赵树理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及其小说,在现实农村大众的精神生活中战胜不了“地头文学”。因此,赵树理发现了“五四”启蒙话语和现实民众在沟通上的隔膜,知识精英所提倡的文化理念和国民改造根本就无法通达中国的乡村世界,又何谈启蒙?于是,立志做“地摊文学家”,拉近文学和乡村的距离成为赵树理自觉的创作动因,这也成就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