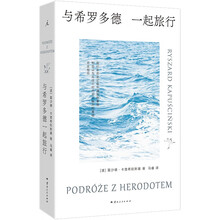由此出发,可以见出近代以后自西方传人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便身负着内外兼顾的双重使命,亦即处在国家建造与族群整合的两头压力之中:一方面要在极力挤进以“民族一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世界体系中展开——主要是与西方列强的——“国别对话”,另一方面又得完成自身内部从传统帝国向多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
独具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之路,在我看来,其在早期主要由梁启超等“维新派”发起的“文学革命”推动。“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借助文艺复兴后西洋文学所体现的“民族本位”精神来促进天朝民众的国族凝聚。这种凝聚在经历了晚清革命党的排满潮流——“逐出鞑虏,恢复中华”之后,逐渐向民国时期的“五族共和”转变。其间还有过一阵从东西方交往互渗的假说里展开对“华夏源流”的大讨论及与之相关的“炎黄图腾”新书写。这些讨论从20世纪初开始,持续了一百多年,代表作品有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1903年)、缪凤林的《中国民族西来辨》(1925年1月)直至沈松侨、孙隆基各自撰写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1977年)和《清季民族主义与黄帝崇拜之发明》(2000年)。
不过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一批“新文学”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等人开始倡导汉语“白话文”写作和“目光向下的革命”。在此过程中,他们虽然强调在文学及文化上大量译介域外、学习西洋,乃至不惜呼吁推翻传统(“打倒孔家店”)或“全盘西化”,并由此展开对汉民族内部士大夫经典的扬弃和批判,却忽略了如何在由传统帝国继承或遗留下来的多民族共存基础上,处理内部的族群差异及表述与被表述问题。作为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在撰写影响甚广的《白话文学史》时,不仅坚持“中国即汉”的立场,抛弃华夷互补的多元性,甚至沿用旧时传统中的狭隘“中原中心观”及“大汉族主义”,主张“以华化夷”。胡适明确写道:“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更早一些时,梁启超总结晚清以来的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便以类似的笔调区分过“非我族类”的满洲统治者与中原的汉学正统。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与此同时,一批具有民族学和人类学背景的学者前赴后继地开展了对中国在族裔、地理和文化上之多样性的描述和阐释。如芮逸夫、凌纯声及吴文藻和林耀华等。这些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不但重新梳理传统文献对华夷互补的论述,而且深入民族和边疆地区进行实地的田野考察,通过以个案深描和民族志书写为特征的学术重建,体现并发扬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对族群多元性予以肯定的另一条路线。在这条路线中,不但出现了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人》那种对中国版图内东北稀少族群的文化描叙,也出现了芮逸夫等对西南苗族通过口头传承的古歌实录。更值得指出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这条路线的激发和带动,民国以后还出现了“非汉族群”在文学、文化和历史上的自我表述。比如内蒙古乌兰夫的《蒙古民族的发展特点与解放道路》、黔东北杨汉先的《苗族述略》、《大花苗歌谣种类》,以及湘西石启贵的《湘西苗族实地考察报告》等等。这后一类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述,不但补充了其他学者在材料和视野上的不足,而且极为重要的是从观念和格局上扩展并改写了既有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
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开始强调“民族团结”的国家政策。“文化革命”时期这一政策被阶级斗争的新方针全然取代。直到1980年代后的重新“改革开放”以及国内各民族成员在身份认同上此起彼伏的自觉和复兴,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学识别与文学史书写问题就摆在了再次复出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面前。问题的难点何在呢?依我之见,就在于如何在多层面的文学及文化关系上,协调现代中国对外自立与对内整合间的有效平衡。
1958年,作家老舍(满族)在为中国作协理事会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早已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相处与交往中,创造了我们整个祖国历史与文化。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今看来,老舍的这个判断依然是今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进行中外比较时不可逾越的重要基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