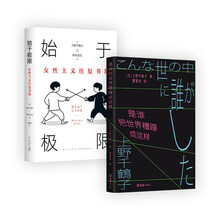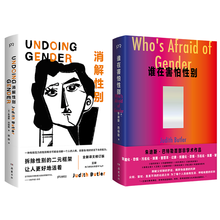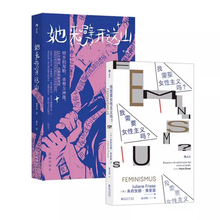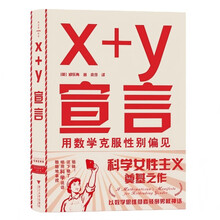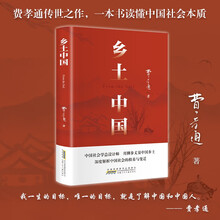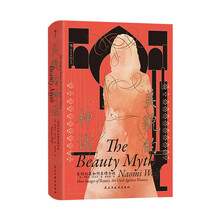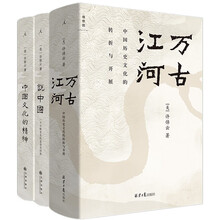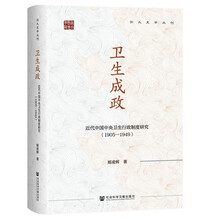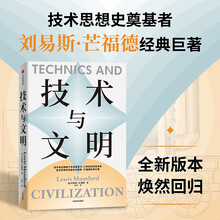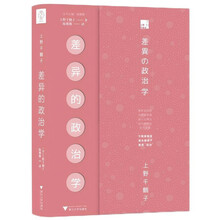《现代城市社会与文化丛书:社会学的政治想象》:
在卢梭看来,之所以要制定契约,是自然状态维持不下去了。只有当自然状态不能维持时,社会才有存在的需要。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失衡呢?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得人和人之间需要帮助和结成群体,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的理智和才能发展起来。原初状态被打破,人的心灵日益开放。就此,通往所有不平等的道路都被打开了。在不平等之下,人和人之间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权力关系由此产生,法律和政府被建立起来了,这样就导致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在卢梭那里,订立契约的主体是“孤立个体”,社会是经由社会契约的过程而形成的,没有这个过程、没有“孤立个体”之间的相互承认,我们就始终处在自然状态。
卢梭对契约形成的解释并不能使涂尔干满意,涂尔干认为卢梭没有阐释清楚契约行为背后的社会条件;卢梭笔下的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的“神圣一刻”,具有十分神秘的性质,甚至是一种人为的虚构。卢梭将社会与个人人为地割裂开来,社会的确立成为一个神秘的过程。在涂尔干看来,契约是指:“所谓契约,唯独指那些个人之间通过自己的行动意志所达成的共识。”(涂尔干,2000:169)卢梭的“契约团结”理论是对历史的虚构,涂尔干再三强调的是,社会契约不是经由“孤立个体”之间的协商而达成的;相反,契约背后的精神根据是社会,个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如果没有社会的依据,则无法得到承认和实施,甚至根本就无法订立出来。这就是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反复提到的“契约中,也并非一切都是契约的”这句话的含义。因此,社会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背后,只有它才能够为契约赢得尊重,契约本身无法为契约赢得尊重。“但是我们最好要记住,契约所具有的维系力量,倒是社会交给它的。假如社会并没有认同契约所规定的义务,那么它就会变成只具有道德权威的纯粹许诺。所以一切契约都假定,社会存在于当事人双方的背后,社会不仅时时刻刻准备着介入这一事务,而且能够为契约本身赢得尊重。因此,社会也只能把这种强制力量诉诸具有社会价值的契约,即符合法律规定的契约。”(涂尔干,2000:76)这意味着,权利上的相互限定只能在理解和和睦的精神中才能得到实现。从孤立个体出发的社会契约论,无法证成社会契约得以尊重和实施的内在依据,在涂尔干看来,契约的内在根据来自于社会的意识和认同,契约和法律只是社会意识的表征形式。
涂尔干既反对卢梭所设想的社会基于契约而形成的构想,也反对斯宾塞所认为的,社会来源于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中自然而然地确立起来的理论。前者虚构了个体和社会,形成的团结与社会分工毫不相涉;后者则无法导致道德关系的形成,正如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利益相互的接近,只是瞬间的事情,无法达成恒久性的关系。涂尔干要做的工作是,在看到契约关系发展的同时,更要意识到非契约性关系的发展。涂尔干通过对婚姻家庭法律的研究,来说明所谓的契约背后的社会性是指什么。涂尔干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契约关系发展的同时,非契约关系也在不断发展。例如婚姻和收养关系、家庭法规都更多地带有法律的性质,而非契约的性质。“总而言之,家庭义务在不断增加的同时,也慢慢具有了一种公共性质。原则上讲,这些义务的来源非但不是契约;相反,契约的作用倒是在不断缩减。换言之,社会对这义务的干预和解除等控制手段在发生改变和不断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环节社会的作用在逐渐减小。”(涂尔干,2000:168-169)在契约背后存在着社会性支配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总而言之,仅仅有契约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来源于社会的契约规定,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契约的作用不在于创立某些新的规范,而在于把预先规定的规范转变为各种特殊的情形;其次,契约没有,而且也不能有约束当事人双方的能力,除非某些特定的条件得到确定。”(涂尔干,2000:173)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