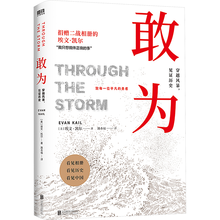其实如果说什么波希米亚香港,蔡炎培与其同代的诗人昆南、戴天、画家蔡浩泉、王无邪等哥儿们应该算是第一代波希米亚香港人。走进蔡诗人独居的寓所,欣见凌乱如昔——我当然没有亲眼见过昔日的蔡诗人,我想见的是那一个遥远时代的纵酒长歌之夕,凌乱的是生活的面孔,因为凌乱而充满生机与神秘。
在堆满各种诗集和小说的饭桌上,空出了一张A4纸大小的位置,那里放着一摞白纸和一支钢笔——蔡炎培无论写诗写文还是抄稿,都亲自手写,别说电脑了,影印机、传真机他都不用。在这个网络时代,我邮箱里唯一能收到的实体书信,就来自蔡炎培,抬头必写某某某诗人收,读之就如互通天地会暗号一般的光荣。
蔡炎培和我天南地北聊天,常常离题远奔,谈名师、名士,谈情伤、情傲——当年多少人被他诗歌中兼有的温柔与孟浪之姿所倾迷!但他就像他所私淑的诗人吴兴华,独来独往,自恃一身才华与傲气,不惜碰钉与寂寞。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他又有这样一种痴情,是与所谓英雄不同的、一种甘人地狱的大悲悯所在。
“我接触到吴兴华才觉得这个人才有资格做我的老师,他很深沉。我熟读他的《秋日的女王》、《记忆》、《绝句》、《十四行》……都能背出来。我是很挑剔的,觉得诗的文字和节奏必须很讲究,吴能满足我。他的重要在于承先启后,是新诗运动最重要的诗人。”素未谋面的吴兴华曾经救他一命,“那时我因为感情问题几乎崩溃,出现幻听幻觉。那时我从台湾读书回来,BlueCoat要离开我。”Blue Coat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女子之一,告别的年代、分开的理由从来不需诉说出口,唯叹天以百般磨难成就一诗人而已,“直到我在文学杂志读到吴的《论里尔克的诗》[编按: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德国诗人],马上感悟了,诗歌晋级了,写出一系列的好诗来。我没有见过吴兴华,但私淑他是老师。”
从此他学会了豁达,虽说仍然想兹念兹,念兹在兹,他也就将此道一以贯之。“我一直这样走,我是一个跟着命运走的人,别人会计划什么,我不会,即使如今这个年纪也如是,我一直感谢上天给我能够走到今天的机会。”爱情、写作、还有赌博,成为他生命中最自豪的事情,我想起的,是他的那句妙语:“写诗如花钱,花完便算。”爱情呢,他倒不这样洒脱。
赴台湾求学,蔡炎培开始拼命写诗,寄了一首《创世纪》去,马上被刊用了,当时香港有几个诗人被台湾看到?诗歌给予他的台湾岁月极好的回忆,“我在台中念书,路过台北的时候就会和那里的诗人会面,叶维廉介绍我认识痖弦和洛夫。我还记得一次在淡水河畔,我拿《离骚》给他们看,大概是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之间。在淡水河畔吃烤肉,痖弦和洛夫问我:‘在那急流河畔,满月在扶光之中’何谓之‘扶光’?我说,现在满月,它的光像水一样,快要满泻,但是因为有张力而不泻,所以像扶住光一样,他们说有道理,作出一个要颁给我学位的姿势。”那夜之后,痖弦送他上车,对他说:“炎培,我们的文坛是有希望的。”这句话他至今还记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