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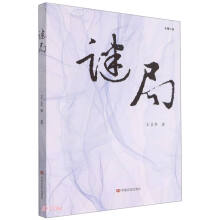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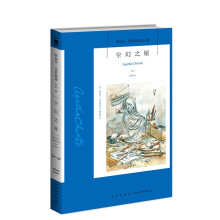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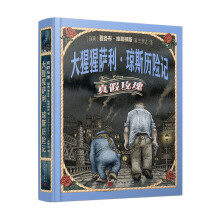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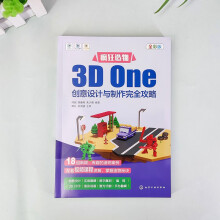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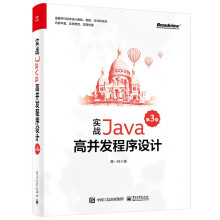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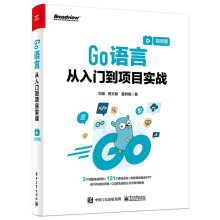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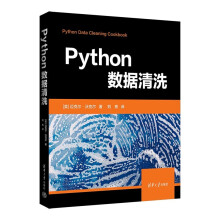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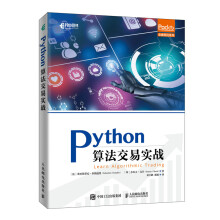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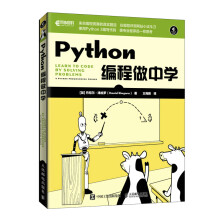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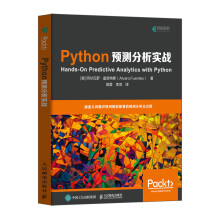
是什么原因让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去制作一枚玉环——一件消耗千倍劳力的陶器的“复制品”?小小的物品中凝聚了超量的工作,成为拥有者对权力的象征性展示。只有从实用器物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不能为其他媒材所替代的、专属的形式上的象征性,玉雕才能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传统。
在几千年的轮回后,人们又回归了蕞原始的目标:发掘玉石的象征意义,通过材质本身的特性,传达对于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的独到见解。
巫鸿美术史文集计划收录作者1979年至今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八十余篇论文和讲稿,按照年代编排,展现作者三十余年的研究轨迹,打破西方研究中国古代美术的传统范式,通过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使这个学科的内涵更为丰富和复杂。对中国古代礼仪艺术的内涵、定义及沿革做了界定,把历史研究的重点还原到古代美术作品的原始功能、意义和环境上去;同时引进多种现代美术史中的分析观念,从“空间性”、“时间性”、“物质性”等多个角度讨论中国古代墓葬、建筑、绘画和器物的基本特质。本书为文集的第一卷,收录作者1979年至1987年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十二篇论文和讲稿,按照年代编排,涉及玉器、青铜器、度量衡器等研究,显示作者出对古代器物和考古材料进行整体解读的技术性研究手段,及以这些手段为中介拓展出艺术作品历史性和思想性的深度。
好古与自发
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中国玉器艺术题材单一。但实际上它和中国画领域一样,也同时存在着许多传统,每一个都发展出了独特的视觉语言,具有特定的艺术追求。4这些传统中的一种是追求古趣,另一种则与其对立,致力于唤起观者感官或情感上的自发反应。
高福履收藏的几件玉雕艺术品是这两项传统的优秀实例。一只宋代玉鸟[图8.5]和一件明代圆柱形带盖玉杯[图8.6]均为典型的仿古之作。玉鸟的原型是汉代鸠杖的杖首,那时每逢中秋佳节,政府会向年及古稀的老人赠予这种拐杖。一千年后的宋代,这种具有礼仪意义的行为已不复存在;鸠杖被视为“古物”而被忠实地模仿。这只立体的玉鸟仅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它的造型有意刻板僵化,鸟的眼、喙和羽毛用概念化的线条勾勒。这个形象显然不是取自真实的鸟,但这不是由于艺术家的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的兴趣并不在于描绘一只真实的鸟。真正吸引他的是来自遥远过去的一个形象背后所蕴含的古老精神:通过强调玉鸟形式与装饰上的“古趣”,他意在将这种精神令人信服地传达给观者。这个目的决定了这件作品从本质上来说是理想化的,反对任何“庸俗的”自然主义的描绘。事实上,一件典型的仿古玉器,无论表现的是动物、禽鸟还是物件,对于创作者与观赏者来说都是指示往昔的“符号”。在这些作品中“古意”本身成为艺术创作的主旨。
16世纪著名玉雕艺术家陆子冈创作的一件仿古器皿模仿了东周至汉代时期一种叫作觯的饮水器,显然带有同样的好古情怀。这个器具的装饰效仿了青铜时代的设计程式,在雷文图案的背景上刻有一龙,以饕餮为三足,杯盖顶部亦装饰了四只盘旋的小兽。但是这件作品的“古意”不仅仅在于将这些往昔的母题作为其题材,更重要的在于其艺术风格:器物的柱体外形,动物图像对称的布置,厚实的杯壁,连同严格的几何图案和神话中的龙,一起营造出一种刻板和节制的效果。事实上,这种风格几乎可被视作仿古传统存在之理由(raisond’etre)。与任何理性的艺术典范一样,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不近人情”的抽象和完美。
如果我们将收藏中的另外两件玉器—一匹玉马[图8.7]和一对玉鹅[图8.8]—加入比较,就会对仿古作品的特点得到更为深刻的理解。这两件玉雕与上面讨论的玉鸟及玉杯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们“自然主义”的形式,还在于它们所传达的细腻情感因素。卧马将头放置在伸展的前腿上,脖子稍向前伸,马腿微微弯曲。马的外在特征—眼睛、鼻孔、鬃毛和尾巴—以浅浮雕表现。这里没有锋利的线条:柔化的细节、玉石的微光以及蜿蜒流畅的轮廓传达出温驯的感觉。这种情感特质也同样表现在那对相互依偎的玉鹅身上。通常被认为是一公一母,这两只禽鸟尾部的深棕色印记似乎进一步突出了它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称这种玉雕风格为“艺术再现”似有误导之嫌:这些动物形象与自然主义的近似并非源自对于实物的精确描绘,亦非艺术家有意表现生命体真实的外在状态。相反,玉马与玉鹅来自一种确立已久的玉雕类型。其他两件类似的卧马玉雕—一件来自唐代,另一件则出土于一座晋代墓葬—证明这一母题具有悠久的历史。5在我看来,高福履所藏玉马之美学价值并非源于对真实原型亦步亦趋的复制,而是来自艺术家赋予这只玉马以类似作品中鲜见的细腻的情感状态。因此,我们若是必定要为这种风格命名,那么“形象主义”(imagist)也许更为恰当。与抽象、冷漠的仿古雕塑相反,这一类的玉器都具有实在的形象,并试图表达一种特定的情感或文学内容。创作这些作品的热情与仿古传统有着不同来源:它们旨在激发作者与观者间自然的情感联结,而非从往昔获得古意。
这两种风格都能被回溯至中国玉器艺术的早期阶段—甚至在商代就已经有两种相似玉雕风格同时存在的情况。6例如在安阳妇好墓发掘的大批玉器中,不少饕餮面具、龙和其他神话动物表现出一种高度程式化的风格。另一种则是以蝉、兔、象、马等动物雕刻为代表的“自然主义”风格,栩栩如生且没有神话及抽象元素。后一类中的一些动物甚至带有某种好奇的面部表情,也许能够被视为拟人化倾向的证据。这第二种风格持续至下个世纪并发展成为具有影响力的艺术题材,但第一种风格的延伸却并不能被简单地称作仿古。中文里的“仿古”一词不同于“模仿”或“复制”一件古代作品。它意味着发掘遥远过去的艺术形式,并运用这种形式来表达一种“当下的”艺术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仿古”的含义类似于英文中的“拟古主义”(archaism)或“古典主义”(classicism)。学者们普遍认为仿古玉雕发端于宋代,进入明清时期后势头更盛。然而考古证据表明,仿古的传统至少能追溯至公元前7世纪。1983年,河南光山发掘了一座古墓,所葬之人为黄君孟夫妇。7墓中出土的54件玉雕器物中,有三件反映出中国早期玉雕艺术中的仿古行为。其中一件是一个立体雕刻的人头,其头冠顶部平坦、两端朝下内卷。[见图8.9a]我和林巳奈夫均认为这类例子属于龙山时代。8类似人像出现在一对被断定为东周时期的玉珥上。[见图8.9b]由于这三件玉器共存于黄君孟夫妇的收藏中,东周玉珥上的独特人头母题应源自其新石器时代的祖先。
这对东周仿古玉珥的制作也许是出于黄君孟夫妇对上古玉器的个人欣赏,因为仿古传统在宋代时才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艺术运动。从北宋时期开始,一群古董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艺术创作的中坚力量。通过他们对古代艺术作品的收藏和分类等活动,玉器及青铜器的“理想”形式必须在古代礼器中找寻的这种观点开始盛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宋及以后朝代的仿古作品并不是对于古代物件一丝不苟的还原。图8.6所示的筒状玉杯是一件典型的明代仿古玉器,但展现出艺术家对于玉色变化的惊人敏感,这在其周汉时期的祖型中是找不到的。另一点需要强调的是:仿古传统从未取代玉器艺术中的其他风格,而是不断吸收新的视觉元素以丰富自身。值得一提的是,当仿古加入了玉器艺术的主流,它与其余玉器传统间的界限也就变得愈发模糊,艺术家也开始将来自不同传统的风格元素进行糅合,创造出新的变体。高福履藏品中的一件黄玉制成的动物合体,有龙的躯干和狮子的尾巴,并饰以花朵图案。[图8.10]这种神话动物通常可以在仿古雕刻中见到,图8.11中的玉兽是一件很好的标本。然而,这件黄玉雕刻的动物有着熊一样的脑袋;宽阔的前额和直勾勾的圆眼睛为它的脸部增添了一丝好奇的、几乎是孩童般的神情。藏品中的一件鹅形水器—它的盖子被做成了一只小鹅的形状—也很成功地将不同风格进行了融合。[图8.12]这件作品明显地受到古老鸠杖的启示,它的拟古主义特征也通过高度程式化的翅膀与头部展现出来。但是两只禽鸟温和的表情又抵消了拟古风格的死板与冷淡:它们慵懒地将头歇在背上,脖颈弯曲的线条添加了精致的典雅,大小两鹅间的亲密关系亦通过并置及呼应得到富有意趣的表现。
象征意义的变化
玉璋在公共及私人收藏中屡见不鲜。这种如权杖般的斧形器很少反映形制与装饰上的变化,其标准样式以长而窄的璋身和“把手”组成,两侧有齿状凸起,中部穿有一孔。许多玉璋以黑玉制成,不少具有超凡的薄度,一些刃处的深色玉石甚至被打磨至透光。高福履藏品中的黑玉璋[图8.13]就是这样的一例。它由带有橄榄绿沉积的黑玉制成,修长的刀刃呈轻微弧形,向前延伸至锋利的末端。另一头的“把手”则稍稍偏向一边,两侧的钩形齿状物与刀刃边缘衔接流畅。
这些作品的年代和起源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个谜。韩斯福(S.HowardHansford)在1969年说:“至今仍未有出土证据,能够对关于这件玉器的起源及用途的诸多猜测进行澄清……”9那志良在为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中国玉器所编写的图录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10然而那氏的图录还未出版,陕西省神木县石峁村就出土了两件类似的玉璋,一件有精致的“齿”,另一件则没有。它们与高福履玉璋有两处共同点:拉长的璋身与黑色的玉质。11发掘者认为石峁玉璋来自新石器时代末尾的龙山文化晚期,可能与商代早期重叠。近日我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教授请教过这一断代的可靠性,他对此确认无误。
汉代的《史记》提到了这种黑色玉璋特定的礼仪功用:周武王在打败商朝、攻入其都城后,举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仪式来确立他的胜利:他来到暴戾的商王及其两名恶妃的尸首前,向每具尸体各射三箭,又各刺上一剑。最后用一把“黄钺”砍下商王的头,用一把“玄钺”砍下妃子们的脑袋。12这里的“黄钺”应是青铜斧头,而“玄钺”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黑玉璋,因为当时只有这一种斧仗是用黑玉制成。这一推断可以在吴大瀓的著作中找到支持,他将这种物件确定为“牙璋”,在《周礼》中这是一种礼制武器,形状类似圭,但有齿牙区隔刀刃与把手。最有意思的是,这本礼书称“牙璋”具有“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的功用,与《史记》所载“玄钺”的用法相互参照。13
这些玉璋特定的形制、颜色及象征意义代表着中国玉雕史上的一个关键性转变。需要指明的是,玉斧自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200年)和良渚文化(约公元前2800—前1900年)时期以来就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但早期的玉斧[图8.14]除材料以外与普通石斧基本相同,并未流露出对形式的特殊关心或对颜色有意识的甄选。对比之下,黑色玉璋的象征价值不仅通过其材质的天然特性、更通过它们的外形体现出来。它们扁薄狭长的璋身,有时呈“丫”字形的刃部,花瓣状的精致齿牙,立刻与任何实用器具划清了界限。因此,这一礼制用具的关键意义在于从视觉上将自己与普通工具区分开来,其独特的形制和颜色进一步强调了它的特殊地位。这一发展在玉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绝对不可低估:因为只有当玉雕从实用器物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不能为其他媒材所替代的、专属的形式上的象征性后,它才能成长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传统。
在中国文化里,一个视觉符号一旦成型,在很长的时间内往往鲜有形制上的变动。玉雕尤其是如此。玉斧作为权威的象征,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被持续制作,长达三千年之久。另一个例子是玉蝉这一象征性母题,指涉着周期性复活的含义。许多公共及私人藏品中都收有汉代玉蝉。这些小型玉雕的原型可以自商代墓葬中找到。河南大司空村在20
世纪50年代发现了一只玉蝉,妇好墓中则发现了石蝉。后者有着圆圆的眼睛、用双线条刻画的颈部与合起的双翅。雕刻者将这种昆虫的形象概括为抽象的椭圆形,并将其特征通过简洁的曲线刻画出来。类似的形式特征也出现在高福履藏品中的一只黑色玉蝉上。[图8.15]类似蝉这样的玉雕母题从古至今持续存在,但它们的具体意义则根据不同时代的信仰与文化的转变而变迁。如果说新石器、商、西周时期的玉器更多反映的是政治及礼制的目的,那么在之后的东周到汉代,玉雕则越发与道家对不朽成仙的追求以及儒家的道德教化观念联系起来。蝉在道教的理想中象征着人的复生。对于儒家来说玉器则象征着最高的美德。汉代学者许慎(30—124年)在他著名的字典《说文解字》中这样定义玉:“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14他所用之比喻的是儒家的君子。必须强调的是,许慎在这里所说的“玉”并非天然玉石,而是经过了人工雕琢的玉器。因为只有通过耗费时力的琢磨、抛光,玉才能“润泽以温”、音色“舒扬”、“理自外”而“可以知中”。因此当人们接受了许慎所描绘的这种象征传统,他们实际上是为玉器作品的可取形式、玉石原料的选择及制作工艺设立了标准。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纯净洁白的玉石越来越被视为玉的最佳之选,而柔和无瑕的抛光技术也受到极大青睐。
玉雕的这种特定观念在汉代之后变得极为盛行,极大地影响了玉器艺术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到明代时,新出现的艺术理想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一批文人学士发起了一项新的艺术运动,批判传统手法的艺术创作。通过强调玉器艺术的天然无饰,他们意在创造一种新的形式,以传达他们对于自然与艺术的关系的独到见解。玉器因此成为这些文人才情抱负的象征性寄托。
高福履藏品中的几件有趣的作品印证了玉器艺术中的这一新潮流。第一件是一只文人案头的笔洗。[图8.16]这一浅钵状容器由淡灰绿色玉石制成,在器壁、器底及器口的一些地方保留了玉石的棕色外皮,口沿的不规则形状大略依照石材表面天然线痕的走势。艺术家将装饰性元素减至最少。实际上,像之前带盖玉杯所展现的艺术与技术上的发展,到明代已至顶峰,但在这里却大半被抛却了。文人们在此欣赏的是一种类似“原始”的品质,将自己与那些只懂得欣赏人工美的“芸芸众生”区分开来。这种趣味通过不同的形式得到表露。高福履藏品中有一座以纯白玉石雕刻而成的山子。[图8.17]整件作品上不见任何市面上流行的山石雕刻上常见的装饰,甚至连树木或人物都没有。毫无修饰的石材给人一种冰冷的裸露感。雕刻家所使用的所有技法都是为了将这座玉雕转化成一块“天然山石”,而这种对于玉石本质的追求揭示了一种不同的独立精神。当这种追求发展到最后阶段时,任何技术都会成为多余,需要做的只是将玉石以几近自然的状态呈现—雕刻者只需为石头做最外层的抛光,让饱满的色泽透露出来。[图8.18]这类玉器有时是受到禅宗影响,目的在于打破所有的传统规则,将观者置于新的境地,让他们迅速地从整体上把握一件作品。因此,似乎在几千年的轮回后,人们又回归到最原始的目标:那就是发掘玉石的象征意义,通过这种材质本身的特性来表达人们自己的文化和思想。
总序 阅读巫鸿 郑 岩 001
1 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 011
2 谈几件中山国器物的造型与装饰 025
3 秦权研究 035
4 三盘山出土车饰与西汉美术中的“ 祥瑞”图像 067
5 东夷艺术中的鸟图像 093
6 早期中国艺术中的佛教因素(2—3 世纪) 115
7 中国绘画中的“ 空间”问题 179
—西方对中国早期绘画艺术的思考
8 传统与革新 189
—高福履藏中国古代玉器
9 从地形变化和地理分布观察山东地区古文化的发展 205
10 四川石棺画像的象征结构 223
11 汉代艺术中的“ 白猿传”画像 243
—兼谈叙事绘画与叙事文学之关系
12 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 267
巫鸿并未把艺术品作为多样而变化中的世界观的图解。相反,艺术品在他手里成为了历史中的演员和创造者,而不仅仅是历史的标志物。——伊万兰·卜阿(Yve-Alain Bois,哈佛大学美术史与建筑史系前系主任,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巫鸿先生在解读中国画史名迹时不仅注意重新审视传统的读画方式和内容实质,还充分注意到绘画媒介形式的物质性特征,将绘画置于一种由创作者、观赏者共同参与动态过程,从而丰富和提升了鉴赏这幅名画的内涵和意义。
——赫俊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