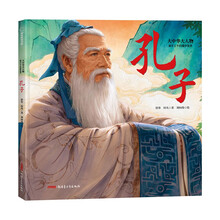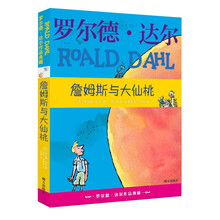《烽火中的水晶球 童年目光里的战争岁月》:
水晶球我到南京的第一夜就睡在被妈叫做“炕”的那张大木柜子上,以后的几年它就一直是三哥、四哥和我的睡床。被子和褥子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又硬又破,面子上全是补丁。南京的冬天可比上海冷多了,我跟四哥分头睡一个被窝筒,脚贴着对方的屁股互相取暖,睡到后半夜,我冷得缩成了一个团儿。但我还是睡得很沉很熟,直到被一个声音给吵醒了。
“咦——呀——”声音发自前院,像是我在上海隔壁邻居家那只关在笼子里的夜莺的鸣啭,响亮、圆润而优美。
天好像还没有亮,房间里黑得很。
声音重复了好几次。
“这是谁在吊嗓子呢?”三哥也醒了,躺在被子里问。
“好像是三姨太的声音。”睡在帘子那边小床上的姐姐回答。
夜莺宛宛转转开始唱起来了:“我心中正难忍一团火性,他弟兄却又来任意欺人,我若不撕破脸皮发个狠,要保我的清白就万不能……”她唱的我完全不懂,只觉得她在生谁的气。
三哥说:“是京剧呢?”姐姐肯定地说,“就是京剧,红楼二尤,尤三姐的唱段。”什么京剧?谁是尤三姐?我根本一句也听不懂。
三哥问姐姐,“你怎么那么熟悉?”“这有什么?原先在南京的时候,戚家戏班唱戏,我听得多呢。”这时睡在大床上的妈妈说话了,“掌若说得对。
她比洪武大十三、四岁,战前的事情她记得清楚。”掌若是我姐姐的名字,大了之后我才知道是“掌若明珠”的意思,至于姐姐说的什么“戚家戏班”,妈妈说的什么“战前的事情”,我听都没听过。
“我怎么不知道?”三哥又追根寻底地问。
“那阵子你才多大?比现在洪武大不了多少。”妈妈回答。
“姆妈,”姐姐问,“戚家后来还有消息吗?”妈妈叹口气,“都失散了……”突然,从昨天到现在一直沉默不语的爸爸莫名其妙地大声说了两声,“该死!该死!”然后又是死一样的静默。
我们都不知道爸爸说的是什么,到底谁“该死”?谁也不敢问,谁也不敢说话。
前院里的夜莺还在鸣啭,“那一日赖家盛宴开,悬灯结彩播歌台,柳湘莲家串一曲惹人爱,那失落的英雄别具悲怀……”这一段我就更不懂了,就只觉着很好听,像是在曲扭拐弯儿的小巷子里绕,每绕一段,就有一个新的景色在前面。
窗外的天色渐渐亮了。
“姆妈,”我喊,“我要起床。我要撒尿。”我其实心里是想出去看三姨太唱戏。
妈妈赶紧起床,给我穿好衣服。我发现,衣服都换成“新”的了——在上海穿过的一件也没有,我被套上了一件叫“棉袍”的衣裳,这样子的衣服我在上海见都没有见过。它的扣子是一个个小布疙瘩,像伸着的小脑袋,让对面的布圈套套住它们的脖子,这才算扣上了。后来我听人家说,“纽扣”,就是一“纽”一“扣”,指的就是这个。它们一溜儿排在身体的右侧,扣起来特别麻烦,尤其是右边腋下的那个扣儿,右手要弯起来,很难够着,特别难扣,非得妈妈帮着才能扣上。棉袍是旧的,别人穿过的。是新是旧我从小就懂,它跟“炕”上的褥子、被子一样,都是又冷又板,就像是小人书上画的武士们身上披的铠甲。更要命的是妈妈还要在外面再套上一件罩衫,说是可以干净点。这件罩衫布都洗得泛白了,中间还有个大补丁。妈妈又把那条围巾给我围在脖子上,再在我头上套上一顶破旧的毛线帽子,说,“外面天冷,别冻着。”我当时并没有想过这些行头是从哪儿来的?直到今天当我重新回忆起当年的这些生活细节时,我才估猜可能是大伯的“赠予”。
我看自己已经穿戴好了,便兴奋地想往前院子跑。妈妈又把我叫住了,说,“前院子是人家的,玩玩可以,切不可进人家的那道圆门。记住了吗?”我点点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