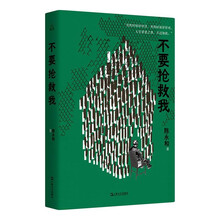楔子
谭美颐不飞了。
除了妮娜、若希和在停飞申请上签字的经理、书记、航医知道,她没告诉乘务部任何人。
过了细雨纷纷、行人断魂的清明时节就是谷雨了,4月16号那天,最后一班飞行,目的地是韩国的鹤山。
以前她总是幻想着不飞那天会是多么多么不寻常,鲜花啊、泪流满面啊、解气痛快啊,都是脑子里曾经蹦出过的画面。可这一天真的来了,却跟以往的每次飞行一样平静自然。
美颐不爱浓妆艳抹,可是单位总会隔上一段时间就来次仪容仪表大检查。一到检查的时候,检查员们和各个中心领导一周七天轮流值班,从早上六点开始,每个出港、进港航班的乘务员都难逃他们的法眼。
不许留长指甲,只能涂肉色指甲油;长发不可以有刘海儿,不许戴黑色的大片卡,只能戴黑色小细卡子;不能涂亮色珠光的唇彩,耳钉不能超过豌豆大,不能戴假睫毛,不能戴有颜色的美瞳,腮红口红必须在机舱的灯光下依然鲜艳,颜色以大红、粉红、紫红为主;不能穿自行购买的丝袜和高跟儿鞋,如果觉得公司发的鞋不舒服可以采取垫鞋垫儿或者忍着等方法。
化妆室是去年新装修的,四面全是明晃晃的镜子,橱窗里放着发胶、摩丝和吹风机。美颐把脖子上的丝巾向外扯了扯,照照镜子,腮红还是有点儿淡,跟舞台上唱京戏的比确实淡了点儿。
还有五分钟就开准备会了,她从黑色飞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支口红开始涂抹,这可是颜色最深的一支口红,专门为飞行而准备的绛紫红。
乘务长的头发不知道打了几层摩丝,发丝跟钢丝似的贴在头皮上。也是,现在不把头发归置好了,在飞机上忙起来是顾不得的。
一切都是正常程序,安检的姑娘们唰地从后腰拿出“凶器”,开始在乘务员身上扫描。那种带红外线的黑家伙在美颐身上上下游走,贴着文胸的钢托扫来扫去,滴滴滴地响。
美颐闪了个身说:“离胸远点儿行吗?”
安检姑娘很正经地说:“这是我们的规定。”
然后黑家伙又开始在肚子上扫描,她没处躲没处藏,想着:唉!完了!这得杀死多少颗卵子啊。
上了机组车,前方就是一条康庄大道,直奔一驾波音777客机驶去。
飞机在起飞以后二十分钟巡航高度达到一万米时开始平飞,五十分钟后已经离开国境飞跃黄海上空。一小时十分钟的时候机长从驾驶舱里给出了准确的落地时间和地面温度,告知三十分钟以后在鹤山机场着陆。
乘务长收回了头等舱一位旅客的茶杯,对美颐说:“十分钟后落地广播,我去经济舱转一圈,广播后把旅客的衣服还了。”
一切平静如水,一如往昔,连一点点涟漪都没有。
飞机已经开始靠近鹤山境内了,透过弦窗望下去,层层峦峦的山峰被大海包围,细雨密密打在弦窗上,无声无息。飞行员们都说鹤山机场对飞行技术要求很高,尤其是降落。鹤山地形四面环山,飞机只能从一个山缝通过,当地的天气条件也不好,靠近大海,没风的时候经常会起雾。
美颐翻了一下广播词上的日历:“咦?今天是4月16号?十年了,正好十年,太快了。”
十年前的4月16号,美颐刚刚飞行两个月,胸前的服务牌上写着“实习生”。
那天的乘务长叫董明珠,在全乘务部是出了名的严厉。美颐生怕出错,提前二十分钟坐在准备室里傻等。罗丽丽路过时向里面张望,笑着问:“跟老董一起飞?”
美颐认得罗丽丽,她是一分部最年轻的党员,优秀个人,服务标兵,刚二十三岁。
美颐是个十九岁的实习生,脸蛋子上一边一块大粉红,她点头朝罗丽丽挤出一个笑。
准备会上董明珠问美颐波音747-400CB飞机一共有几个水灭火瓶,她一紧张脑袋一片空白回答说:“不知道。”乘务长镇定地说:“四个。”又问她有几个海伦灭火瓶,她瞎编说:“十个。”乘务长敲了下桌子说:“张妮娜,你告诉她有几个。”妮娜说:“有六个海伦灭火瓶。”
准备会最后,董明珠对全体组员说:“航空飞行安全第一,没有安全任何都谈不上,让旅客满意放心的服务是建立在安全之上的。对于应急设备的掌握不能出丝毫纰漏。”
董明珠一头蓬松的鬈发行云流水般绾在脑后,她微微昂起下巴,如同一只骄傲美丽的狮子。
飞上海的航班大满客,乘务员们忙得快成了八爪鱼。将要落地前的五分钟,董明珠突然用内话机通知区域乘务长到飞机一号门。
不一会儿,区域乘务长熊刚回来了,“咕咚”一下重重坐在座椅上,神色凝重。美颐当年并不能体会什么叫凝重,只记得熊刚一直盯着机窗外,嘴角倔强地抿着,后槽牙的咬肌鼓得像含了乒乓球,他脸上没表情,不知不觉掉了两滴泪。
美颐还是个实习生,心中不敢有旁骛,反复默念着培训部老师教的应急脱离口号:“系好安全带,低头,弯腰,紧迫用力。”
回程上客的时候,有个中年平头男士走到美颐面前,神神秘秘地问道:“哎,你知道了吗?”
“先生您坐哪排?”她还没反应过来。
“你们公司摔飞机了,在韩国鹤山。刚刚半小时的事儿,我朋友就在韩国,人家那边都知道了。”平头男压低声音说,额头上冒了一层小汗珠。
美颐愣住了,客舱乘务员手册里针对特殊情况的处理中没有关于如何回答旅客提问摔飞机的规定。她扭头问妮娜:“什么意思啊?”
妮娜“霍”地一下拉她到卫生间门口,小声说:“咱们公司出空难了!刚才乘务长通知他们到前面开会,肯定说的是这事。驾驶舱里收到地面的通知后第一个就会告诉乘务长。”
“乘务长怎么没反应呀?”美颐还是不解。
“坠机的乘务长张凤霞和她是同一届的。”
起飞以后发餐前饮料,美颐使出吃奶的劲儿拉着饮料车一排一排发水,董明珠从头等舱过来了,她气定神凝地站在客舱通道中。
平头男要了杯咖啡,董明珠倒好咖啡,稳稳地递到他面前,雍容地笑着说:“先生您的咖啡,请拿好小心烫。”
平头男满脸不自若:“咱们飞机能安全到北京吗?”
董明珠微笑着回答道:“我们的飞行员是全民航技术最好的,您不用担心,肯定能平安到北京。”
人鬼殊途,阴阳两隔。坠机的是你二十年的同事,你不难过吗?美颐看着她想。
董明珠在带飞记录本上写的评语最后一句是:微笑服务工作要加强。她对美颐说:“小姑娘,干乘务员这行任何突发的事情都能遇到,只要你一出客舱就要始终面带微笑。”
那天回到乘务部大楼才真的感觉到出事了。领导们忙着开应急会议,派遣室里挤满了乌泱泱的人,刚飞回来的一进大门就捂住嘴流泪,两个乘务员在楼道里碰见了,面对面聊着聊着开始擦眼泪。
妮娜指了下说:“你看,罗丽丽她爸。”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被搀扶着走进大楼,腿脚颤颤巍巍挪着步子,一双痛苦的眼睛欲哭无泪。
今天早上罗丽丽还笑着问美颐,短短几个小时,她却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的日子里,经常会有记者过来采访,领导们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稳定扎实搞好飞行,努力团结共渡难关”。
单位没有公开善后处理的具体事宜,普通乘务员的知情途径来自于新闻媒体和小道消息。党群办公室组织大家搞征文活动,美颐积极响应,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为蓝天献青春》。
空难中生还的两个乘务员其中之一做了美颐的督导员。
经历过生生死死的人,有种独特的平和,从没见过他和别人红过脸,找他请病事假,能批的一定会批,实在批不了的,不苛责也不啰嗦,直接带着乘务员找到更高一级的经理说明情况。似乎从内心深处有种能体恤人性的本能。
有次谈话,美颐看见督导员两鬓的几丝白发,她想就这样一个平常人,既不高大也不伟岸,在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后,被甩出机舱几十米开外,爬起来又跑回废墟背出几名旅客,直到飞机残骸烧成大火球,眼看着和他一起的同事们葬身火海,粉身碎骨。
灾难来临时,每一丝希望都是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每一个生命都无比珍贵。
中方殉难的机组成员共有十人。培训部的黄老师代表殉难者家属到鹤山领骨灰,一把大火早已让他们化骨扬灰,只能用残肢断臂来确认DNA。
黄老师把乘务长张凤霞的骨灰盒紧紧搂在怀中,喃喃道:“我是来接你们回家的。咱们回家。”他的眼泪啪哒啪哒滴在骨灰盒上。
在异国他乡一块烧焦的土地上,几块飞机残骸静静地躺在那里,上面写着:B-00025。
四季更迭,时过境迁,人们在五味杂陈的生活中淡忘了空难,乘务部也搬进了用花岗岩砌成的新办公楼。
悠悠生死别经年,杳杳魂魄入梦来。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和美颐素未谋面,却穿过同样的宝石蓝制服飞来飞去。
美颐想:反正最后一班了,爱谁谁了。没人再提起你们,我悄悄地祭奠你们一下吧。
她不想用那种故意抑扬顿挫的声调,索性将广播词置在一边,拿起广播器静了几秒,把心一沉,向全体乘客娓娓播出她飞行生涯中最后一段广播: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将在二十分钟后到达鹤山国际机场。请您打开遮光板,收起小桌板及脚踏板,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
“鹤山有小雨,地面温度是20摄氏度,68华氏度。请您随时添加衣物。
“现在正是谷雨时节,当年被烧焦的土壤中早已拱出新绿,一架架飞机在这里安全起降。当您下机时,将看到雨润万物、生生不息的景象。
“祝您在鹤山愉快!”
“啪!啪!啪!”坐在三十一排的男人,沉默着鼓了三声掌。他叫墨子文,三年前认识美颐。人生有时鬼使神差,明明已经断了的两个魂儿,以为此生此世不会再见了,偏偏又要碰见她。见到了又能怎样呢?他的妻就在身边。
他没有叫她,她的样子一点儿也没变。听完广播,他心下惘然:原来我从来没有用心听过她的声音。
……
展开